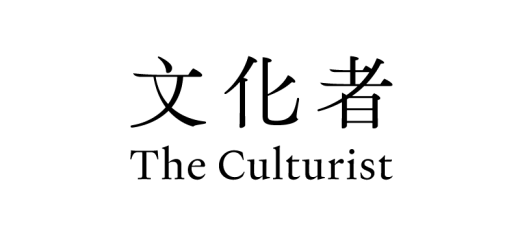「以前我的確有啲睇唔起香港,運動令我看清楚⋯⋯年輕人認為食得飽、着得暖、人工揾得多之外,原來更重要是物質生活以外。我在這個年紀見到呢個景象我覺得好幸運。」── 陳育強
創建於1963年的香港中文大學,以孔夫子《論語》中「博文約禮」為校訓。諷刺的是,激烈的抗爭轉入校園,中大被冠以一個新朵:「暴大」,並成為抗爭者與警方對峙的重要地點。
2019年11月12日之後中大二號橋後像一個冷酷異境,更似結界。過千粒催淚彈、數不清的汽油彈横飛之後,淺灰色的地面被染成黑色,從此這世界的顏色也不一樣。
今年「陸六」的陳育強對這個熟悉又陌生的校園,百感交雜。他畢業於中大藝術系,任教於中大藝術系25年,與這所大學共榮共辱近半個世紀。暴力帶入了校園是「果」,是誰令碧海也變?變作俗流滔天?荒謬的是,連校長段崇智救學生都捱了滿臉催淚彈。
「文革;1988年政府推行大學四改三;1989年八九民運,中大都走得很前,我當時做學生都有走出來。奇怪是這傳統現在城市化和消費改變,而不是以前的純樸,昔日為追求真理和公義,一吹雞便出來有義氣,現在校園不是個個都是這樣,要遇到埋身的事才能覺悟。」
陳育強清楚記得,於美國鶴溪藝術學院獲藝術碩士學位後回中大任教時,他只有二十多歲,還是個青澀的「死𡃁仔」。那年,1989年,中大的大紅花盛放,跟北京廣場上一樣的血紅。

「當年的你不是秃頭吧?」我戲謔。
「頭髮不知有多濃密。」陳育強回話。
無腳的雀本來只計劃教一個學期便離開,他主講西方媒介創作課程。「最後卻足足教了25年,有些科目未教過,當時沒有機會備課便硬着頭皮去教。第一個學期很辛苦,教現代美術,但我無讀過歷史,兩小時的課我花很多時間去備課。」陳育強苦笑道。
三年前,陳育強提早退休,兩次告別宴學生來了過百人,不少人送給他的禮物,都寫着四個字:「一代宗師」,他顯然是個桃李滿門的教授。
早前跟陳育強到德國柏林,與一班準大學生參加遊學團。走在布蘭登堡門附近的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Memorial to the Murdered Jews of Europe),二千七百多根大小不一的混凝土柱排列佇立,像橫躺的棺材又似迷宮。學生們在裏面逛着,思考這城曾發生的歷史,戰爭的殘酷,陳育強從藝術角度,引發學生思考。
和大部分香港人一樣,進入催淚年代,對香港的想像也完全改變。但作為春風化雨的夫子,看見有學生被冠以暴徒、被拘捕,他的感慨自然更深。另一方面,作為一位「走得頗前」的年青人的父親,默默地支持兒子,他有雙重的感受。

中大原學生會會歌,由黃永熙作曲,林以亮(宋淇,即張愛玲好友及其遺產執行人,宋以朗父親)填詞,其中一句是:「我們要做替大眾鋪路的橋樑。」2017年,中大學生會代表會成立《廣東話會歌、會章專責委員會》,為會歌填寫粵語版歌詞使會歌更有香港文化,新會歌變成:「披着荊、斬着棘/堅信初生犢需打拼過千關/如夢的初衷心底裏渴望。」
曾經做過學生,也教過無數學生,他理解學生的訴求。
「作為『和理非』我比較抽離,嘗試去明白成件事,也成日問自己:『我可以做甚麼?』唔明藍絲咁多證據不可信仍會信政府,一直諗。」這種「可以做甚麼?」的無力感,延綿整個香港。
或曰:沒有嚐過催淚彈放題,不算香港人。和理非的陳育強當然也吃過催淚彈,因為知道自己勇武不起。「坦白講我不是很感性的人,但我身邊學生與朋友好多都覺得,乜角色都應該返去,我比較抽離。某程度我覺得自己勇武是阻住人哋。無貢獻仲要人照顧我?」
他在社交媒體或whatsapp 群組發言,希望可以影響社會、一個社群,甚至一個人。
「不進則退,拜託唔好企喺度,唔好比人傷!」
「年青人條命一定長過佢地,呢D就係本錢,唔好傷本!」他發表言論,希望大家理性去看待事件。
「我諗最成功是Be Water,把整個格局放在國際議題,香港人往後應更了解Be water 是什麼意思?效用大過燒舖和搞美心。現在一方面建立黃色經濟圈對抗藍色經濟圈,用攬炒話俾既得利益者知,我們是生命共同體,無論是藍是黃。還有更重要是:深層次矛盾要如何解決?政府根本無解決過。」
陳育強另一個身份是香港藝術家。他曾參與逾百個展覽,包括第51屆威尼斯雙年展、第二屆亞太當代藝術三年展等。他也曾擔任《香港視覺藝術年鑑》主編多年。現時仍是Para Site藝術空間及香港美感教育機構董事局成員,以及為亞洲藝術文獻庫和雅禮協會擔任顧問。

陳育強多年來依隨直覺來創作,他坦言,整個運動也讓他重新思考藝術的力量。「以前我對藝術與政治藝術好有疑問,事件有讓我改觀。」
看到香港人天天迸發的創意文宣、大戲版《願榮光歸香港》、催淚彈頭藝術裝置、獅子山人鏈、越看越有味道的政治漫畫,遍地開花甚至國際開花的連儂牆,都令這位藝術家和藝術教授側目。
「黃照達已好勁,尊子無得頂,呢兩個漫畫家已經好勁和有創意,視覺和政治口號乜都有齊,最成功是連儂旗,它代表了香港咁旺盛咁有色彩。感情+技術+效率,高手在民間,這就是香港的隱形創意核心。」陳育強侃侃而談。

1989年,陳育強開始教學生涯,他還記得九七前後討論文化身份,成為世界注目點,二千年新生代,身份不被明顯地提出,作品看到製作方式的生態,越來越放鬆,好多空間可以鑽入去。沒有空間直接在城市做作品,不是我是香港人才去做,默認方式來做作品。新一代白雙重,李傑,政治環境轉變是一個很大的議題,勾起藝術家對政治興趣,例如周俊輝。香港人對回歸政治現實的反映,不再define香港人,回歸幾年後,講如何自處,流露在作品中。
陳育強說,從來在藝術教育上,並非教學如何生存。「我自己都無簽畫廊,我自己都生存唔到。我會感化他們將自己觸角批到很敏銳。」
陳育強說,很多同學都認為他太理性,不夠浪漫。「藝術家大情大性,浪漫角色,我不是。我在大學已諗如何客觀理解藝術,因為藝術教育比藝術家重要,如果教出幾個藝術家只能自己圈子發揮作用,畢業學生如何發展,可能得10%做藝術家,90%要找其他出路。我盡量將藝術的專業打開,同其他知識有聯系,需要更多想法克服這多元東西,再進入藝術界,這些年做了很多思考。」

「人生到了這個階段,你覺得整場運動對你個人有甚麼影響?」我問陳育強,這也是我問過無數活於平行時空的人的問題。他想了想,很認真的回話。
「人生走到這一步,香港一直話是福地,引以自豪的價值是錢和財技,一講就是經濟。現在看清楚,這些舊一代價值只是香港政府的價值,新一代的價值迴異:他們認為食得飽、着得暖、人工揾得多之外,原來更重要是物質生活以外。」
陳育強更語重心長地補充:「以前我的確有啲睇唔起香港,運動令我看清楚,對與錯已變:你上到位,贏到人就是對?現在已不同。一直香港人給外界感覺是市儈、膚淺、短視和自我中心,你現在看Facebook論述幾有水平,年輕人又關心國際事務。香港視野大好多,香港不只屬於中國,而是屬於世界。」
「香港教育都唔是太失敗,我在這個年紀見到呢個景象我覺得好幸運。」

提早退休的陳育強,即搞了一個展覽「不如重新開始」。他坦言正在回歸原點,努力創作。「覺得自己返老還童,我好珍惜不為什麼去做作品,不為做作品而做作品,我好享受。」陳育強說。
撰文:鄭天儀
攝影:余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