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幅叫《黃衣人之死》,旁邊戴口罩的人,在哀悼他。」藝術家小雞口中的黃衣人是梁凌杰,2019年6月15日他從高處墮下,經搶救後不治,終年35歲;牆上熟悉的臉孔,還有終年22歲的大學生周梓樂的側面;遭香港警察射爆右眼而引致右眼永久失去視力的印尼女記者等。當然,並非所有臉容都具名,例如2019年「831太子襲擊事件」中,那些地上求饒的市民、那些催淚煙中前行的黑衣人‥‥‥
今年2月,台灣版畫藝術家李迪權(小雞)與葛尹風(Ivan Gros)再度合作,策劃了一場圍繞「白色恐佈」的版畫展覽,並取名「棍」;當中的創作理念,來自眼見香港警察用以打壓群眾的——警棍。
作為創作者,二人從不避談政治話題,早前他們參與發起〈反可愛宣言〉,對抗以可愛之名,實質不願面對真實的人們。如宣言中所提到:既然藝術有心要再現真實、呈展世界的每個稜角,它的缺陷便和美好一樣重要,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藝術才具有意義。
白色恐怖 黑色抵抗
展覽設於台北古亭站附近的cafe,走上三樓,率先映入眼簾的是一頭犀牛,凖備衝向雨傘狀的蟑螂大軍;面對犀牛的步步進逼,有蟑螂戴上「豬嘴」,起弶迎戰;亦有一些不敵先天差距,慘被輾壓成蟑螂片。戰場以外,有個令人熟悉的畫面——蟑螂從高處遊繩而下,下方是牠們的手足。

這幅畫是葛尹風為了配合小雞今次的主題,特意創作的作品,畫上有兩句醒目的中文「白色恐怖 黑色抵抗」。他將「白色恐怖」的警察變形為犀牛,呈現暴力常態化;而示威市民,則變形為警察口中「黑鼆鼆」的「蟑螂」。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犀牛的巨大體型與細小蟑螂的巨大對比,某程度上亦是權力的象徵的體現。

將示威市民當作蟑螂,是一種去人性化手段,他解釋:「卡夫卡以蟑螂來體現極權專制中的暴力常態化,還有對人性價值的否定。」至於犀牛,則是參考尤涅斯柯(Eugene Ionesco)以犀牛形象表現暴力常態化,帶出隱藏的白色恐怖。
一切從「612」開始的恐懼與心安
如果葛尹風的筆觸是風,表面不着痕跡,實質早而留下裂痕;那小雞則是火,那是一種恣意伸展的張力。仔細觀察,這對合作夥伴有很多對立,如同版畫的黑白相煞;同時也是一種默契。
二人當中,只有小雞去過香港示威現場。去年10月,小雞在香港逗留了數天,為是次展覽找靈感;回港後他「反芻」現場記憶,刻畫出50幅他印象至深的畫面;最後再花了一個月時間籌備,邀請葛尹風合作,促成眼前展覽。小雞指,他選擇「612事件」作為第一幅作品,止於10月理大之戰:「因為612是第一場警民衝突,我打算畫100張,現場只有一半。」

他提到港鐵太子站外的經歷,令自已對恐懼的想像,不再停留在實質的暴力。「那天我去了港鐵太子站外的悼念處,打算拍張近照,突然有人朝我大喊,『不要拍呀,你拍到我的臉,我會被失蹤會死掉你知道嗎?』」 原來,對方是每晚負責在站外換花,燒衣的人。「那時你會感受到,民眾在恐懼。」所謂白色恐佈,就是當下他與對方置身同一空間下,突然感受到的恐懼氛圍。

「那你有去過黃店嗎?」我突然想起,2019年10月正是黃色經濟圈開始冒起的時期。「朋友有帶我去,他們都會選黃店,當時店內全世界都在罵!」那是恐懼鑽不進去的安全所,至少暫時不能,原來白色恐佈下,人們的安全感只能凝聚在一個陝小的空間。「本來,我打算2月6日去香港,搞一場版畫快閃,途人可即場印畫再帶走,可惜遇上肺炎。」話到此處,他有點「抌心口」。
無臉的女囚 從歷史審視現在
小雞選擇感受現場,然後刻畫現場;葛尹風則選擇透過刻畫歷史,審視現在。

多年前,葛尹風由法國到台灣定居,身兼版畫藝術家與法國文學系教授的他,版畫多以短文或詩為輔。他喜歡以隱喻帶出信息,這位法國文學家的浪漫,融合於他的藝術當中。如同他於展覽中,以雷文斯布魯克集中營為主題的版畫,手法亦是一貫的隱喻。納粹德國時期該集中營位於柏林北邊,1939至1945年期間,該營曾羈押過13萬名女囚,最後僅約4萬人倖存,連原來的三分之一都不及。

其中一幅畫名為《木板房》,刻畫了集中營惡劣的居住環境。隨着被關人數上升,寢室愈來愈擠擁,最後發展到每21名女囚,需共分一床架。葛尹風筆下的女囚無臉,有些更不直接刻畫身體,由黑灰線條與留白交織而成,留待讀者想像。
集中營與香港事件,兩者關聯是白色恐怖。「雖然我們的事件、手法、時間、空間、文化,全部不一樣,但我們的本質性是相同的,大家都在訴說一種白色恐怖。」小雞道。
創作者與現場的距離
兩位藝術家在同一個空間,以自己的方法與距離,呼應自己,也呼應群眾。對二人來說,藝術並非無病呻吟。小雞指:「一切都是表現自已,既然你有這個衝動,一定有原因。實行時,不管你如何逃避,你的潛意識都會走出來。我覺得大家對藝術有太多浪漫的想像,其實它跟說話一樣。就是這樣。」葛尹風的看法是,「與文字相比,影像傳遞信息的能力很強,後者的普及性更大,不易受制於文化。」畢竟語文有着先天的侷限。

他們眼中的藝術很實際。「我找到適合自已的媒材(木刻版畫),再透過它講話,講得更精準,讓人可以印象深刻,印到腦海;那就功德圓滿了。」小雞如是說。當談到藝術的療癒力,葛尹風有所保留,他認為藝術本身無法消除恐懼:「很抱歉地說,我認為藝術本身並沒有這個能力;但我們身在其中,卻可以自我圓滿,人對周遭要敏銳,只有這樣文明才會出現,社會才有機會變好。」
二人的藝術世界裏,不浪漫,從來不是罪名。
棍/gun展覽
日期:即日至3月14日
地點: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77巷7號1-3F(小路上 藝文空間)
營業時間:上午12:00 – 下午7:00(週一公休)
撰文:湯珮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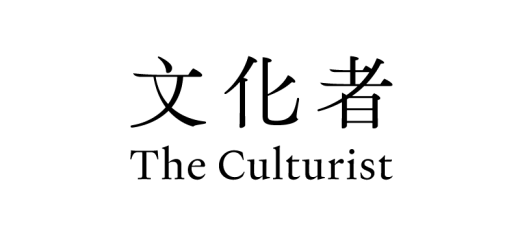

.jpg)
.jpg)

拷貝-1.jpg)


.jpg)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