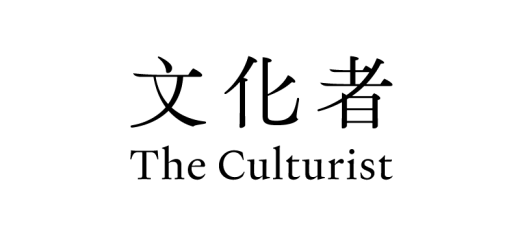藝術不僅是一個寓言,它更可以是一個預言。
「其實那幅畫所畫的並非武漢協和醫院,而是武漢市十一醫院,稱之為『協和』只因當年武漢人有個口頭禪——不行,就去協和。」曾梵志透露其90年代初成名作《協和醫院》系列的名稱由來。其實不管武漢協和也好,醫院武漢市十一醫院也好,曾梵志的想像力就算如何天馬行空,亦難料到在接近30年之後,因為新型冠狀病毒疫病爆發,作為疫情風暴中心的武漢當地醫院竟赤裸裸地重現了,其筆下《協和醫院》系列所描繪怵目驚心的景象。
在舉國一片抗疫輿情中,曾梵志早前亦向湖北美術學院教育發展基金會捐贈100萬元人民幣,又另分別向武漢協和醫院和金銀潭醫院捐贈50萬元人民幣,用於支持武漢抗擊疫情及疫病防治工作。在接受國內媒體訪問時,他表示:「武漢是我的故鄉,我的親人和朋友都生活在此,我的根也在這裡,本來今年春節要回家看父母,結果止步於疫情爆發。這段日子我難過、焦慮又感到自己能做的很有限,最後決定一是向偉大的醫務工作者們表達我的敬意,二是作為校友給深陷疫情的母校鼓鼓勁。希望疾病盡快退散,大家能咬緊牙關扛過去。」
發揮深邃的藝術批判作用
創作於上世紀90年代初的《協和醫院》系列,是曾梵志藝術生涯早期階段的最重要作品,其呈現當時中國社會的病態與人民百姓的渺小與無助,至今仍在發揮深邃的藝術批判作用。「前幾天,無意之中看到武漢臨時醫院的照片,很多病床放在一起,我確實突然又想到了這組作品。當時經歷的氣味、聲音和場景一下子重現了。這種感受很複雜,我意識到一種木然的痛苦,日常快樂的蒼白和淺薄……我想最近這段傷痛的記憶應該是會刻進好幾代武漢人的心裡了,由此我們或許應該真的思考一下自己未來應該做些什麼才能讓這個城市變得更好,能為下一代年輕人帶來一些什麼改變。」曾梵志在訪問中表示。

早在2003年,藝評人Karen Smith在論述《協和醫院》系列時便指出,醫院是一個恰如其分的符號,因為當靈魂離開了塵世,這種公共機構本身就往往成為血肉之軀最後的安息之所,作為一種隱喻,它本身同人們中間疾病或是社會盛行某種病毒的傳言聯繫在一起,「也許在藝術家心裏,醫院的隱喻有助於他思索一些問題:給肉體帶來懲罰的罪孽究竟是什麼?父輩的罪惡傳給他們的後代,就像許多中世紀祭壇裝飾畫中所刻畫的,而且這一切又如何在缺乏宗教信仰的時候得以指認和澄清。什麼人或什麼事,因為誰的名義招來了報應,並且在朝向生命最終遠逝之日的道路上要教導什麼?看起來有一段時間困擾着曾梵志的那種對於疾病的感受是無法治癒的,也不可能逃避…這些主題似乎都同武漢直接聯繫在一起。」
源自醫院廁所的藝術傑作
曾梵志1964年出生於湖北武漢的一個普通家庭,父母都是一家印刷廠的工人。初中畢業後,曾梵志亦曾一度在印刷廠當工人,其後在朋友影響下對繪畫產生興趣,公餘往青年文化宮習畫,在多次前住上海和北京觀賞西方藝術大師展覽後,深受西方表現主義、抽象主義及觀念藝術吸引的他決定復學,最終更考入湖北美術學院。曾梵志在上世紀90年代初畢於湖北美術學院油畫系,其創作以其獨特的語言風格和敏銳的社會批判,受到評論界廣泛的讚譽,被認為是當代中國較具代表性和國際影響的藝術家之一。其代表作包括《協和醫院》系列、《面具》系列、《肖像》系列及《亂筆》系列,均備受國際收藏家賞識追捧,2013年更憑《最後的晚餐》於蘇富比拍賣會創下逾1.8億港元的成交價,刷新在世當代中國藝術家作品拍賣紀錄。

儘管名滿天下,曾梵志從不諱言自己卑微的出身,原來當年他畫《協和醫院》系列時,正家住武漢市十一醫院旁,因家裡沒有廁所,每天要跑醫院借用廁所,正是在那兒,曾梵志目睹人們排隊候診的擁擠、焦急與茫然;病人出事,醫護搶救的情景。所見所聞的這些場景最終觸發起他的創作靈感,成為在他表現性的冷酷筆觸下,眼神呆滯而驚恐,手部被不合比例地誇大、骨節突出的神經質的人物形象。《協和醫院》系列先後有三組的三聯作品,當中《協和三聯畫1號》1991年發表於藝術家於湖北美術學院的畢業展上,畫中所表現普遍人類生存狀況在精神與肉體上的痛苦不安,率先得到了中國著名藝術評論人栗憲庭的賞識。
刻劃心靈摧殘的人群
栗憲庭曾以「殘酷」來形容這個時期曾梵志的畫風,「以醫院為題材,在寫實的外框下突出形象的象徵和意象,以及筆觸的表現力…在表現性的筆觸中,把隱藏著的血腥與危險透露出來。」栗當時正協助漢雅軒畫廊負責人張頌仁策展「後89中國新藝術」展覽,便給張頌仁引薦了曾梵志。張頌仁以每幅2000美元的價格買下曾梵志4幅畫,並邀請他參加「後89中國新藝術展」。我的藝術導演兼攝影師朋友Ringo Tang與曾梵志相識於微時,當年他隨香港漢雅軒畫廊負責人張頌仁在栗憲庭的帶領下來到曾梵志位於武漢的工作室,就是在那間醫院旁小屋裏,Ringo為年青帥氣的曾梵志在其新作《協和三聯畫2號》前留影,以作為張頌仁推廣在港舉行的「後89中國新藝術展」之用。

1992年,曾梵志攜《協和三聯畫2號》參加廣州雙年展,並獲得優秀獎,當時批評家祝斌寫下了這樣的評語:「《協和三聯畫2號》以新表現主義極有表現力的油畫語言刻劃了一批心靈遭到摧殘的人群,在滯呆的形象中可以感受到藝術家筆下的善意與同情心。語言與母體統一在恰當的宣洩中,這是藝術成熟的表現。」《協和三聯畫2號》在曾梵志藝術歷程中里程碑之作,他選擇了西方宗教畫中常見的三屏格局,呈現出宗教式的悲劇感及崇高感,中間一張更以米開朗基羅於梵蒂岡的《聖殤》雕像為靈感。曾梵志早年受德國表現主義的影響在這作品中可謂顯露無遺,鮮明的顏色對比及強而有力的筆觸,讓藝術家把自己帶入到每一個醫護和病人之中,作品所包含的表達方式,諸如痙攣的手、空洞眼神、以及被撕裂的、血肉模糊的人物身體等,把藝術家對題材埋藏的情感澎湃宣洩。
藝術典型觀照普世苦難
曾梵志說:「我所畫的每一張畫,其實提出的都是一個問題,人的問題,從生到死的一系列問題、人所面臨的所有困境。那時我天天都看到醫院裡那種排隊候診的場面,看到病人出事、搶救的情景,從醫院聯想到人生很多相似的東西。我忽然覺得,這就是我要畫的那種感覺,我想應該畫一組這樣的作品。」曾梵志以人文關懷的視角平視受苦的眾生,對普世性的苦難作出感同身受的表述。正是因為受到此種藝術典型啟發,《協和醫院》系列壓軸作,同樣創作於1992年的《協和三聯畫3號》,不但為這早期重要系列劃上完美的句號,在藝術語言上的個人化更為曾梵志的《面具》系列埋下了伏筆。2013年,《協和三聯畫3號》在香港佳士得上拍,以1億港元天價落槌,1.13億港元成交,成為曾梵誌第二件拍賣過億的作品。

跟其後成為跨文化符號的《面具》玩世不恭、隱喻嘲諷的藝術態度截然不同。《協和醫院》系列揭示了曾梵志努力呈現出更根本的人性和更深遠的意義深遠,人們可以從此系列三聯畫作看到,以世俗的方式體現卻近乎宗教信仰的一種人類靈魂的救贖。就如Ringo Tang所言:「1993年到訪曾梵志在武漢協和醫院側邊的畫室,適逢其時正值曾梵志刻畫人間疾苦的《協和醫院》系列之時,似是預警今天的世情,滄海浮塵,芸芸眾生,無奈地面對命運,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只有堅守信念,一切皆能安然過渡。」
藝術家要保持基本良知
《協和醫院》系列亦可視作為藝術上的一種靈魂自我拯救。在題為《永不安寧的靈魂—栗憲庭和曾梵志對談錄》的一篇文章中,栗憲庭對曾梵志問道:「作為藝術家要保持人的基本良知,這是作藝術家的理由,你認為是嗎?」曾表示:「這是必需的,我覺得真的應該憑良心去做很多事情。」曾梵志從醫院聯想到人生很多相似的東西,雖然他也畫過一些很漂亮的東西,但他覺得那種東西都是舞台上的很虛假的東西,「就是那種粉紅的和黃的,我其實是想把它畫得特別燦爛,但也特別的虛假,就像舞台上的一種佈景。人都是一種自我安慰,等着誰來拍照的很做作的姿態,包括人的手,一種假裝出來的得意的城裏人的姿態,《面具》這批畫就是這樣的感覺。」

今天我們每日在媒體看到的疫情報告,都將人變成「確診、死亡、治癒」的數字了。曾梵志卻始終傳承藝術家那一份悲天憫人的信念,「這與我從小生長的環境確實有很大的關係,很多各種生病的人呀,還有各種殘疾呀。因為我從出生到來北京之前,都是在那條街上長大的,那條街人的感覺實際上是印在我心裏的。不管我以後怎樣穿西裝打領帶,那些都是些表面的感覺,內心深處的一些東西,給我一些觸動,永遠無法抹去。我肯定要表達、要發洩,或者說一定要釋放出來,這實際上是一種情不自禁的感覺。《協和醫院》系列都是在這樣的狀態中出來的。」

命運無常,信念篤定。年少的曾梵志是內向的,在學校不愛說話,還經常回答不上來老師的提問,班上僅有的三位沒有加入少先隊的學生,他是其中一個。少年時代沒有戴上過的紅領巾,他此刻仍在哀傷。為了更多地補償着這種哀傷,他在後來的畫作中總利用一切機會給自己戴上一條紅領巾。如今看來,假如曾梵志與大老闆 馬雲合作的《桃花源》又或者他為演藝天王劉德華創作的演唱會海報,是那種玩世現實主義的高級「面具」,穿過這些枯藤荊棘蔓延曲折的「亂筆」,我們便依然可以在曾梵志的「協和醫院」中瞥見那一角象徵犧牲與救贖的「紅領巾」。
撰文:Patrick Chiu
攝影:Ringo T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