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機會畀你去10年之後你去唔去?
唔…
如果可以,我反而想返去10年前…
我想同10年前嘅自己講…
你而家做嘅嘢,都係啱嘅。
—— 導演、編劇麥曦茵
這番話是訪問完結後,我和麥曦茵 Heiward 閒聊時偶然講起的。我感覺她人未到四十,但面對自己的人生卻早已踏入不惑之年,面向社會,面向自己,她有自己的一套見解,不過十餘年間的電影路,似乎她更想有人為她拍拍肩,說聲加油。
由2008年籌備拍攝的《烈日當空》,表達對於外在世界矛盾的憤怒,簡單而直接。時至2018年拍攝的《花椒之味》,電影向內尋求和探問改變的空間,在戲內隱隱散發出一份成熟又持重的質感。23歲那年的Heiward 讓一眾修讀電影的學生,以為能達到同樣的高度,如今的麥曦茵,我不曾想像過,她並非磨平了棱角、變得婉轉,只是她找到更好的方式和棱角共存,成為有更多說故事方式的麥曦茵。
兩種方式說故事
「《烈日當空》很直接,而《花椒之味》是很迂迴的。」
回想23歲初為導演的時候和拍《花椒之味》的時間,Heiward 坦言自己的追求,對於電影的想法或是在生活上貫徹的執念不曾改變:「我相信23歲的自己去掌控一個拍攝的時候,可能想營造、想塑造、想追求的更多是在電影本身,而經過這麼多年再拍電影時,可能追求的不再是電影本身,而是電影內外的一些反思。」和導演做訪問就如要逼他們叩問靈魂的深處:自己做了些甚麼?我要說甚麼?

《烈日當空》提出的最大提問是,當年輕人和他們要進入沒法理解的成年人社會或是自身和沒法適應的轉變抗衡時,如何選擇做一個怎樣的成年人;而《花椒之味》是成年人如何面對自己多年積累下來的傷口或傷痕,可以選擇如何繼續走下去。沒錯,問題一直不變,就是我們的人生路該如何走下去?選擇,是甚麼?
《花椒之味》如果、如枝、如樹三姊妹劇照.jpeg?fit=1024%2C576&ssl=1)
「可能《烈日當空》的精神狀態就是,聽不聽到呀,這樣不斷叩門;但《花椒之味》就是不如我們談一談。」Heiward 簡單歸納了兩齣戲的說故事方式,就是由力竭聲嘶的吶喊到持重的溝通方式。
持重就是成熟最可怕的慢性毒藥
「當人到達某一個年紀時,其實有很多事情我們真是不容易很直白、很直率地告訴對方,這種包袱可能就是我們不再是孩童,我們不再年輕,所以我們要有一份自重。」
看過《花椒之味》我想也會認同,基本上你無論如何堅守眼淚,最後還是難以堅持不讓眼淚奪眶而出。這套電影的三姊妹仿佛總有一個是自己的過往,看《花椒之味》就像是直視自己的過去,隨時間線推進,共鳴感亦越趨強烈。訪問後我反而更跳出一個想法,為何我連對流眼淚也這麼自重了,我們的溝通障礙似乎不止對外,同樣是對內,要持重就是成熟最可怕的慢性毒藥。
Heiward 憑藉資料搜集和對於人性的經歷和記憶揉合在《花椒之味》中,書寫出自己所理解原來文本中的人設和關係糾葛,引起不少觀眾的共鳴,「這真是我親眼看見過很多,無論是前輩也好、朋友也好、親人亦好,我們都有些執念是我們無辦法放下的。」她如是說。
進入社會後,大家和《花椒之味》的三姊妹一樣,我們成年了,到了不再有空間去任性或逃離自身的問題的年紀,我們或多或少帶着不同家庭間帶來的創傷,經過歲月累積傷口未必能癒合,或許我同樣都在迴避問題。Heiward 說:「而這些問題全部令她們的表達方法、溝通方法都是帶刺而充滿障礙,轉彎抹角的。」這點不止是戲中的三姊妹,而是所有人都會遇到的問題,只是在鄭秀文飾演的如樹身上更明顯,她甚至帶着遺恨繼續她的人生,直至到她所怨恨的父親死去,都未能放開,這都是溝通障礙造成難以表達的愛,但我們卻用自重美化了它。
Heiward 坦言電影中多少是有她的投射,只是並非她對自身家庭的投射:「其實人設和選擇可能接近二家姐更多,提出的提問亦接近二家姐更多。」二家姐如枝有着關於自我認同危機、尋求身分、存在價值的探問等等的問題,「即使我們面對很多的傷口和難題都好,我們如何透過面對這些問題,然後我們檢視傷口和缺失,從而得到療癒。」我想Heiward 十餘年間的電影路亦是這般走過來。


無法撇除的本身
「我沒有很強烈地覺得任何一個角色是我自己,但可能她們的說話方式我植入了一種我對語言的理解,或是我想這樣處理,變成很容易跌入你一聽那句對白就是麥曦茵。」
訪問時我問過Heiward :「很多人說你的電影就是說青春,你覺得是不是?」她想了想回答我:「這樣說不是很『着數』,反而真正如果說我拍的電影的共通性,可能是自我發現和自我療癒,意思是我都可能會老,我對青春的定義可能會變,應該說那個變幻才是恆常,哈哈,這句說話已經很不青春。」Heiward 眼中的青春未必和年紀有關,接受自己變老和青春其實並無抵觸。
但聚焦在《花椒之味》上,Heiward 坦承這齣戲可能正正呈現了一種在青春末期,我們如何適應這個世界,和有何選擇的想像。
「身處那個大環境當中,我們可能會有麻木或者習慣,或者過度適應而不想轉變,而當轉變發生的時候,我們便會反思以現在自己的狀態或模樣去存活是否恰當,我們還有沒有改變的空間呢?我們這樣下去是否真的好?」電影中不斷的提問就像是叫我們面對現實,而且要擁抱現實,因為從根底裏我們都明白自身要面對的一切問題,放任從來不是解決方法。而接受變老,其實有選擇。


選擇,是甚麼?
「當我們遇到適應世界過程中,有困難有阻礙時,我們才發現原來在我們人生中,我們一直很渴望他們出現的成年人其實從來都是缺席,而不知不覺間我們已經活到我們曾經渴望他們的年紀了。」
人生隨年月漸長,我們無法避免成為上一代,一代人與一代人之間的比較從來都是必然會發生的。「其他人經常說下一代有甚麼問題,有甚麼做得不好,但不,我覺得他們很承擔,甚至他們更清楚如何尋找一個方法去面對自己的人生,或者面對一個其實沒有出口的人生,其實他們準備好,或是說那份準備是他們很早便認知到那種殘酷是甚麼,然後他們才會設法用不同的方法去建立一個新的生存模式,因為整個社會結構或需求已經不同了。」Heiward 如此說。
Heiward 眼中:「由上而下去觀望下一代的慣性,其實是一種衰老和頹敗的表現。」這好像很批判性,但青春末期這是其中一個分岔口,到底要變成那位從來都缺席的成年人,還是擔當那位從來都缺席的成年人。在《花椒之味》裏面,Heiward 並沒有將一些對外的憤怒像從前《烈日當空》一樣投放其中,因為她覺得有很多價值觀的問題她都仍然有所保留。
「我覺得每一個下一代只會不停超越上一代,我覺得我不會變成那種批判下一代的成年人,因為我永遠都處於一種對所有新事物都感到好奇的狀態,然後我會很欣賞現世的人,究竟他們如何疏解問題,如何去理解所有事情,又或是他們如何建立現有的一切價值觀。」因為世界從來都在變,Heiward 接受無時無刻都處可能淘汰的狀態。
當我們必須要融入這個社會,跟隨着這個社會的遊戲規則,一段時間後我們都明白到有很多事情未必是我們跟隨這些規則就能如願,那我們如何面對這份失落或者期待落差呢?在接受成長的同時,面對社會的洗禮,Heiward 以心中的青春定義回應我對青春末期的提問:「我們如何迎擊所有我們過去覺得沒有辦法明白或是沒有辦法接受的一些事實?這不是你接受了就等於認同它,但你先要接受我們是處於一個這樣的現實中,無論多絕望也好,你不否認荒謬與殘酷的存在,其實就是一種希望,因為越去否認越去迴避,就越沒有希望。」
2009年第28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麥曦茵初執導筒的《烈日當空》和新晉導演獎項擦身而過。11年後的2020年,她憑《花椒之味》同時問鼎第39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導演和最佳編劇,問她有沒有想過奪獎,她侃侃擲下六大字:「我不想太多了。」反而如何生活如何生存更是她現在更常思考的話題,不過回想多年的電影路,她還是無悔青春。

撰文:余日一
攝影:陳昶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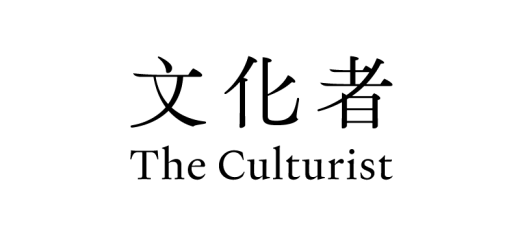








從「烈日當空」到「花椒之味」麥曦茵導演的作品仍舊保留著她獨有的說故事技巧,同樣教人看後會反思 如何面對難以預計的人生 路,兩部作品很沈實地訴說社會現狀, 沒有太多的煽情主義,卻教人看完後,有種心痛的感覺。很欣賞麥曦茵導演的努力,也很欣賞寫這篇專訪的撰文者, 透過字裡行間讓麥曦茵導演立體化,麥曦茵導演仿佛站在你面前細說她對電影路的無怨無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