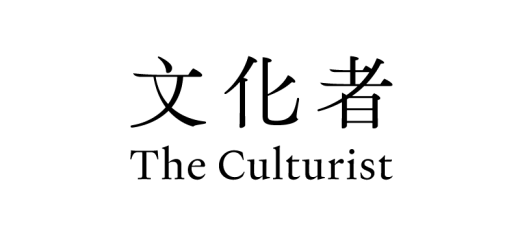早兩星期,我們曾報導過波點女皇草間彌生將在五月於英國舉行個展、以大型鏡房裝置慶祝精彩的九十年藝術路。成功把作品商品化的藝術家當然值得高興,因為這意味着他們能站穩腳步、與觀眾的距離更接近。然而如美國媒體In Other Words 和Artnet News的執行編輯,Charlotte Burns和Julia Halperin去年9月作過有關藝術界性別不平等現象的研究所說,藝術買賣市場長久以來有着「玻璃天花」(Glass ceiling,意指職場裏約定俗成的性別定型限制女性的發展),女性藝術家的作品與男性相比從來不是藏家和美術館的首選。
藝術市場的性別平等有待商榷,何不跳出數字的限制,回歸作品本身以細味女性藝術家的生命故事?趁着今天「三八婦女節」,為大家精選了將在今年舉辦大型個展的各地女性藝術家故事。雖然以往未必常被大眾掛在口邊,但各位「有過去的女人」透過不同形式作品表達的「Women Pride」、以及對女性主義及相關議題的持續反饋,都絕對值得被多加注意。也許往後談起女性藝術家,想起的名字就不只草間彌生一人了。
讓女性從刻板印象裏活過來
談女性的性別氣質,少不免聯想到「華美」和「優雅」等關鍵字,已故中國藝術家謝景蘭是其中一例。1921年出生於貴州名門,父親是文人、祖父是學者,長大後的她也好像很「自然」地考進了杭州藝專音樂系。與藝界巨匠趙無極結婚後,他們於40年代末移居巴黎,謝景蘭也趁機精進音樂和舞蹈技巧。被趙無極徵詢過作畫意見,後來連她本人也投入繪畫創作。

經歷過離婚和改嫁給法國雕塑家,謝景蘭把女性體驗多變人生的感悟融入抽象畫創作。而受她喜愛的電子音樂和現代舞影響,她晚期的畫作充滿山水畫揉合迷幻飄渺線條的風格。雖沒有明顯地以女體入畫,曖昧迷離的畫面卻散發代表傳統女性姿態、優雅的流線型美感;某些與大自然相關、浩瀚感翻騰的畫面,揮筆之勁意外令人聯想起她作為中國藝術家在外地發展的倔強和堅毅,突顯專屬女性的剛柔並濟。她的作品現正於法國博物館Musee Soulages展出至5月10日,展覽裏同場有另外42位巴黎女性藝術家的畫作及雕塑,呈現50年代抽象藝術裏女性所佔的獨特位置。
然而女性的「優雅」是否必然?刻板印象(gender stereotype)是性別研究幾乎「走唔甩」的議題,也是引致藝術界性別差異對待的主因——「男性普遍比女性優越」。你也有這種印象嗎?縱然這或許已不是我們的現代社會有意刻劃,而是從以前已約定俗成而影響至現在。

50年代出生的美國攝影藝術家Cindy Sherman在當時已對社會所安置給女性「應有的形象」表示不滿,前衛的她以硬照作品同時呈現的刻板的女性形象和不甘受限而反擊的女性。
其中最有名的是70年代中後期,由Sherman親身上陣當模特兒拍攝的彷電影畫面照片組《Untitled Film Stills》,以各種華美的妝容和服裝呈現媒體裏給人既定「女性」的優雅形象,然而暗自流露不舒服、彆扭的表情和姿勢,足以表達Sherman對「做戲」有多鄙視;其後Sherman一人分飾兩角,針對性拍攝一系列以符合「男性凝視」(Male-gaze:女性被建構成被凝看的角色,滿足男性預想的刻版印象)的彷色情刊物性感照片。自導自演的她同時扮演「凝視者」和「被凝視者」,以「主動式被動」的手法嘗試在「男性凝視」的權力關係裏,脫離受害者的姿態而取替男性的主導權。在於當時相較封閉的社會來說,這為人們理解女性的性別角色定型提供了嶄新的角度。
Sherman的回顧展囊括了1975至今年年中、近300件作品,其中當然包含上文曾提及的作品。展覽將於4月1日開始在巴黎Foundation Louis Vuitton藝術博物館展出。

打破傳統社會推崇的理想女性形象,還有於50年代抽象主義盛行之時,反其道以現實主義畫風創作人像畫的美國畫家Alice Neel。原就讀於女子美術學院的她以為能擁抱美好的藝術人生,誰知在30年代接連歷經失敗的婚姻和喪子之痛,令Neel曾嘗試自殺,這段時間的畫風也愈趨黑暗(尤以涉及親子關係的作品更見晦暗)。
也許變得「化」了吧,年紀漸長的Neel畫風終於變得輕鬆和直率。從60年代開始她就愛繪畫孕婦的裸體,大膽對外表達自己對女體的詮釋。包含在80歲時曾畫過的自畫像,這批一絲不掛的女體系列身形均不是討好社會、迎合「期待」的。但她執意要為「不完美的女體」平反,而以孕婦裸體為題作畫也被視為Neel坦誠面對黑暗過去、克服心魔的象徵。
Neel的展覽將於6月10日在法國巴黎Centre George’s-Pompidou展出,展期至8月24日。
自主人生
從性別角色定型中解放,也在「男性凝視」中逆襲過來,女性藝術家的目標放得更遠,漸漸更大膽地碰觸以往被視為禁忌的性議題,渴望讓自己走到更為自主的位置。

與Neel擁相似經歷的,是去年曾於香港「法國五月」活動展出的已故法國藝術家Nikki de Saint Phalle。她曾經歷被生父性侵、患上精神分裂的童年陰影。但入住精神病院,卻意外成為打開她接觸藝術的契機。「自學自畫」的她出院後更受第二任丈夫鼓勵,以步槍射擊取代畫筆塗畫,令顏料以充滿爆發力的紋路灑滿在畫布和T恤等混合物料上。這種以行為藝術作畫的方式在30年代來説既是別樹一格,更是讓de Saint Phalle找到以「不傷害人的報復方法」發洩情緒的重要出口,同時更象徵着長大後的她擁有更高的自主性及話語權後,為自己甚至其他受害者對父權暴力進行控訴。
從激烈的藝術裏與黑暗的過去和解,de Saint Phalle的世界漸漸明亮起來。六十年代,愈發能感受生命美好的她感動於好友美國演員Larry Rivers太太 Clarice的懷孕身軀,創作出彷Clarice身形的《Nana》雕塑。眩目的色彩、配飾和手舞足蹈的姿態,為生命和誕生而慶祝,更有歌頌母性的意味。她的舊作即將於4月5日至9月7日在美國紐約Moma 藝術館作展出,亮點之一是受西班牙建築師Gaudi標誌性的大型雕塑影響而創作出彷遊樂場的互動型女體《Sphinx》。觀眾從雕塑私處越過甚有挑戰「碰觸女體」禁忌的曖昧意味,由de Saint Phalle創作更使作品暗示讓女性掌握身體開放與否的自主權。
而於去年10月初以88歲之齡離世的黎巴嫩藝術家Huguette Caland,本月24日開始會由卡達杜哈Mathaf Arab Museum of Modern Art為她舉行紀念展,展期至8月26日。與de Saint Phalle一樣,兩位已故的女性藝術家都關注女性對身體的性自主度。

於30年代出生,也正好於30歲才開始藝術路的Caland,表達方式比de Saint Phalle內斂一點,像知名度較高的作品《Body Parts》就以曖昩的曲線、弧度和浪漫的用色表達女性美;1975年她更參與時裝設計,《Tenderness》連身裙精簡卻見玩味,Caland的設計也勾起觀眾對女性私密部位的聯想,甚有向觀眾鼓勵或教育女體不應被禁忌化的意味。
邊緣中的邊緣女子
在傳統的性別定型下,女性以往被視為邊緣化的一群;時移世易,當性別的距離好不容易拉近了,種族、性向及性別認同等卻是永遠能「分高低」的範疇。南非影像行動者(visual activist,定位上比藝術家走更多一步)Zalene Muholi過去十年來持之以恆在進行的,就是把「邊緣中的邊緣」——南非LGBTQI+群體的生活,透過她的鏡頭下真實呈現。可見女性藝術家除了關心自己作為女性的「進化」,也進而關注被邊緣化群體的需要,希望透過藝術讓更多人一起達到自我實現的階段。

縱然南非是首個通過同性婚姻的非洲國家,當地人對LGBTQI+群體的不了解和恐懼仍未消減;這也代表他們仍在危機下生存,強姦和毒打同志等「拗直治療」也一直發生。Muholi沒有大肆賣弄悲情,只以影像無添加地為南非LGBTQI+群體進行紀錄,把他們真實的樣子呈現。這正提醒世界關注LGBTQI+群體權益——不只空泛的教育,而是從日常事件入手、切身解釋為何某些制度上通過同志相關法律的國家,LGBTQI+群體仍未得到真正的「平權」。
而她的自攝人像系列取了祖魯語的名字為《Somnyama Ngonyama》,大意為「向黑色母獅致敬」,甚有希望扭轉外界常加諸於黑人女性和不同性向及性別認同之恐懼及攻擊,並將之化為正面的鼓勵之意味。她是攝影師、也是鏡頭前的模特兒,她在80多張作品裏除了把自己的臉龐塗得更黑、也把因「多重邊緣身份」而受不公對待的憤怒化成以日常物件製成的不同飾物,每張照片都代表着她的吶喊。
她的作品現正於德國柏林的博物館Martin-Gropius-Bau展出至下年7月。作為性別、性向和種族都曾/正被邊緣化的人,她以一絲不掛的黝黑肌膚和自信且美麗的表情回應,擁抱所有曾被誤解、甚至歧視的身分。相信無論是甚麼種族、哪種性別和性向,我們都能從Muholi的作品身上找到不被了解、卻因很想被了解而告訴自己要變得更強的共感。
撰文:熊天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