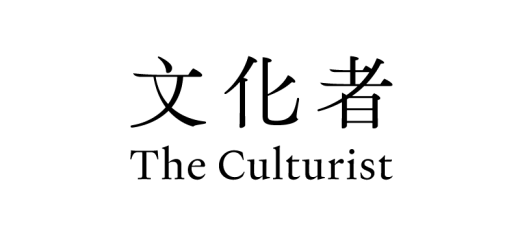「是很不捨的,但到了我這個年紀也沒必要再留了。我這幾幅畫都是相當好的東西,希望有喜歡收藏、識貨的人能承接,給它們一個好的歸屬。」
── 香港著名中國明、清古典傢具收藏家黑洪祿
「是很不捨的,但到了我這個年紀也沒必要再留了。我這幾幅畫都是相當好的東西,希望有喜歡收藏、識貨的人能承接,給它們一個好的歸屬。」—— 香港著名中國明、清古典傢具收藏家黑洪祿
人稱「老黑」的黑洪祿,真的不年輕了。
但活了九十個年頭仍中氣十足,腦內記憶體準成度不輸電腦;對上一次上門拜訪,他還親自下廚炮製一絕的黑家牛肉麵款待我。「幾十年前、一輩子的事情都在腦裡,忘不了,忘不出去的。」黑洪祿指指自己的腦袋笑說。
被滿室木古董包圍着,書與文房亂疊如山,黑洪祿常坐的黃花梨圈椅自然「包漿」得渾厚亮麗,歲月的「加持」令此時、此地洋溢着教父的氣場。黑洪祿是香港著名中國明、清古典傢具收藏家及古玩商,更是已故著名「中國古董達人」、「明代之王」(King of Ming)的安思遠(Robert Hatfield Ellsworth, 1929-2014)1949年首次來港時認識的朋友。原來,改革開放後,安思遠跑遍內地尋名畫,幾百幅捐了給大都會博物館後再展開尋寶之旅,老黑一直是他在內地及香港的「盲公竹」。
談木器黑洪祿自是專家,但原來做古董的觸⻆也讓他練就了一對鑑賞丹青的金睛火眼。與安思遠的跨地域尋寶以外,黑洪祿原來自己也有收藏名畫,而且背後有許多有趣故事,#文化者專訪了這一代人物,聽他說職涯難忘事,還有一段段「畫緣」……
黑洪祿回憶,他是1949年由北京經天津經韓國來到香港,原計劃賺一點錢就回老家北京,想不到一住就七十多年了。「16歲我就在那個親戚的工藝店當學徒,甚麼都做,一點點的學,最初學的是木器,我由打蠟、加工、翻新全部都做,賣給外國遊客。」
結交安思遠 全中國尋寶
1949年前後,香港古董業迎來了第一個發展高峰。由於當時內地時局不穩,許多外僑、華人紛紛轉移定居香港,其中便有大量藏家和行家,香港遂逐步成為中國古董向世界擴散的中轉站。
就在當時,他在香港認識了其第一位外國朋友安思遠,兩位小伙子沒有共同的語言,卻有相同的美學鑑賞品味。「那時候大家很年輕,他大我四歲,他是1929年出生我是1933年出生的。1963年我去美國又碰見他,他是由零起家後來就發達了。」
安思遠據講九歲已開始收藏,19歲的時候成功將一批鼻煙壺售予蒙特利爾美術館(Montreal Museum of Fine Arts),並結識當年收藏界中的女傑Alice Boney。後來,女傑引薦安思遠入讀耶魯大學遠東語言學院,師從王方宇門下,「安思遠」這中文名字正是王方宇所𧶽。
1970年代,香港古董業迎來了第二個春天。這一時期,經濟發展迅猛,香港誕生了大量本土新藏家,醫生、律師、建築工程師、大學教授、企業家等社會新貴入行收藏,香港古董業重地由尖沙咀 移至中上環的荷李活道,一條街見證着香港古董業的發展。
安思遠開始每年來港尋寶大概是1979年。「八十年代他要出一套涵蓋中國書畫、對聯等的專書,他跟我說想到內地買畫買書法作品,就讓我幫忙的跟著他去到各個地方去各個大城市,由南方到北方的文物商店尋寶。」黑洪祿說,這套經典書出版後,紐約大都會博物館1980年給他舉辦了一個展覽展出了兩三百幅他的字畫收藏,然後他就不哼一聲的把那批東西捐贈了博物館。「是!一張也沒留的全部都捐了!」黑洪祿提高了嗓門說。
有趣是,捐完後安思遠又展開了另一輪的收藏行動,當然又找來黑洪祿當盲公竹。「頭一站是北京、天津、西安,之後又去了蒙古、呼和浩特都去過;後來還有雲南、重慶、成都、廣州和香港,我在香港還給他買了很多很多的字畫。」黑洪祿記得,安思遠喜歡齊白石,也掃了許多石魯的畫作,當時齊白石一把扇面賣兩千美金左右,現在已是天價。
黑洪祿回憶,安思遠在中國名家畫作身價還未爆升之時,早着先機趁低吸納,除了捐贈他藏量過多時還會拍賣一部分,「大概拍了不少於兩個多億美金。」
「陪跑」之餘,黑洪祿亦偶有吸納心儀的名家作品,不少畫家當時只是小名家,如今都躍為大師了。「每張畫大概都有故事!」黑洪祿笑說,聽他娓娓道來之時更令人驚訝是,老人除了記得畫作購藏地點外,還牢牢記住了當時他被丹青驚艷的原因,還有故事背後的細節,他都巨細無遺的銘記着。
「我收藏字畫都不是刻意買的,都是偶然因緣分、或者人家給我送上門,背後都有故事。」
眼紅紅的牧羊女
黑洪祿開始說故事,由1956年石魯畫牧羊女的畫作《樹下》開始…… 早在1955年7月,石魯曾赴印度擔任萬國博覽會中國館的總美術設計。這其間他繪畫了大量的寫生作品和速寫,《戴紅頭巾的趕車人》、《印度人家》均創作於此時,畫面中充滿畫家無限創造力,以及對新事物的激情。
「《樹下》是在西安省文物商店買的,我跟那個經理李常慶挺好的。有一天早晨,他說我給你看一張畫,當時我想購藏但他的手下一直跟他搗麻煩說不賣。第二天早晨那李老先生看見我,眼睛血絲給爆了紅,原來他昨天又為這手下生了氣,他就說:『這張畫我就賣給你!』」黑洪祿拍了一下枱,以表達當時李經理發洩的一口悶氣,就這樣他又執到寶了。
黑洪祿收藏徐悲鴻畫1940年畫的《喜馬拉雅山》,除了背景有意思外,得寶的過程也有點夢幻。
在前往大吉嶺之前,徐悲鴻在致劉汝醴信中提到:登喜馬拉雅山乃「生平大願,自慶得償」,登山後徐悲鴻興奮地將這次登喜馬拉雅山稱為「平生第一快事」,激發了極高的創作熱情。在大吉嶺將近半年的時光,他以素描、水墨與油畫的形式反復描繪出不同視角、環境、光線下的喬戈里峰風光。他以雪山為主體創作的《喜馬拉雅山全景》,成為他油畫創作的一座豐碑。
黑洪祿記得,他第一次到西安回民街清真寺附近的鼓樓,跑到樓上去看東西。那年正趕到西安的夏天,下雨下得多,那個房頂都漏水了,一張徐悲鴻的《喜馬拉雅山》就躺在那張大桌子上。「我問這張畫幹嘛?店員說上面漏水潮濕,他們把畫放在桌上給它吹乾。我就問這畫賣不賣?店員說可以賣,差不多乾了你可以買了。」
就這樣,引用「祖師奶奶」張愛玲的一句:「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黑洪祿就這樣拿下了他心儀的「風乾」徐悲鴻早期的大作。「徐悲鴻最擅畫動物,但我購藏這作品卻全是風景,完全沒有動物,沒馬沒雞,我反而覺得很特別。」對於畫,黑洪祿還是有一套自我的審美觀。
傅抱石以畫換書 黑洪祿以家具換畫
另一次奇遇是這樣的,黑洪祿在一位美國朋友那裡偶然看到了一幅傅抱石的畫作《疑是银河落九天》,他甚喜愛,要求朋友割愛。這位周遊列國的朋友賣畫給他時,還附送了這畫背後的小故事。
「大概是七八十年代,傅抱石當年到訪一間在比利時專賣建築書的外文書店,他想買一些西洋建築書,但手裡頭沒有多餘錢,傅抱石就拿了這張畫跟書店老闆換了書。這老闆把畫放在書店很多年,後來就給我朋友慧眼收藏了。」
後來,黑洪祿一樣的慧眼識名畫,向這位朋友求畫。「我當時也沒有那麼多現金,就給他一部分現金、兩三件黃花梨家具。當時黃花梨也很便宜,就給他以物換物了。」黑洪祿認為,能收到好東西,絕對靠緣分,還要有一點點機智。
還有,吳冠中1977年那張《武夷山》,黑洪祿回憶當年在西安市文物商店與此作一見鍾情的情景。「吳冠中用國畫顏料在武夷山寫生,仿著油墨的畫弄畫出來的,意思也挺好,是他早期的佳作。」當年吳冠中帶中央藝術美術學院學生到各地寫生,他視之為「美差」, 也記錄了當地風物人情,以抽象的手法興懷古之幽思。
另外一張石魯的《華山春曉》和潘天壽的《萬歲長情》都是八十年代黑洪祿有緣在香港的三聯書舉辦的畫展上遇上,無寶不落的他一眼見到是畫家的佳作便收藏了,一直珍藏到現在。
「我買東西不是當時買了有水位就賣,像這些畫作我收藏了幾十年一直保存着。」黑洪祿說。
人到耄耋斷捨離 望有緣人承接
人到耄耋,老黑覺得也是時候斷捨離。「是很不捨,但到了我這個年紀也沒必要再留了。我這幾幅畫都是相當好的東西,希望有喜歡收藏、識貨的人能承接,給它們一個好的歸屬。」
回望半生,黑洪祿覺得自己很幸運。「做甚麼事情都得講天分,這是『阿拉』(回教徒的真主)給的。沒有天分與智慧做一輩子還是糊裡糊塗,靠着努力也不行。」黑洪祿口中真主賜的「天分」,說到底是那對懂得分辨好壞的「眼學」,這抽象的絕活必須靠經驗累積加上天資煉成,不斷交「學費」與練功。
「做其他行業有所謂退休,但是做古董這行業經驗越多越不需要退休,是不能退休;由生下來做到最後就完了。」他呷一口清茶,接着說:「現在我可以說退休,或者半退休,因為有第二代能接班的。我沒甚麼期望,他能接班就行了。」他口中的接班人,正是公子黑國強,他也是安思遠的助理兼高徒,後來更自立門戶「研木得益」,並創辦典亞藝博、水墨藝博等藝博會。
黑國強形容,除了安思遠與父親,他有很多「師傅」,「每一件古物都是我的老師。」他侃侃回憶:「那個年代確實是一個美好的年代,我很幸運也是成長在那個年代,作為一個旁觀者,從他們的收藏、談吐與認真看到他們一代人是怎樣生活的,以前在香港叫『古董佬』,但原來做古董佬可以那麼優雅的。」
八十多年接觸過的古董如過眼雲煙,黑洪祿露出一個感性的表情,坦言:「回憶太多、不能盡錄。」見盡風浪,留下滄海一聲笑。
採訪、撰文:鄭天儀
拍攝、剪接:朱小豐
「入木三分見丹青 」黑洪祿先生丹青珍藏拍賣
日期:2023年6月12日(周一)
地點:北京中國嘉德藝術中心
王府井大街1號
(拍賣將出現於「大觀— 中國書畫珍品之夜·近現代」)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請把The Culturist專頁選擇為「搶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