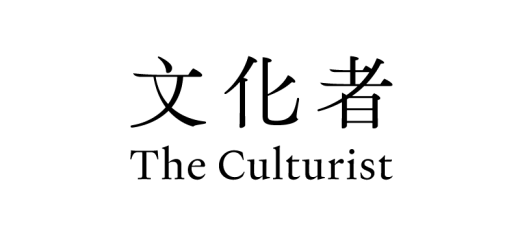(請前往文化者youtube頻道,獲得更好觀片體驗![]() https://youtu.be/LcTrZ6uZ-dU )
https://youtu.be/LcTrZ6uZ-dU )
「詩人窮也好,老也好,他的精神永遠都很年輕。」
──詩人黃燦然
順著紀錄片的鏡頭,在城市的角落或小巷追探香港詩的痕跡,《詩》表面上在談論香港詩人的故事,其實電影本身也未嘗不是一首「詩」。
「這次拍《詩》,對我來說特別有一個正面的意義,因為他們(黃燦然和廖偉棠)令我覺得,一個人要能保持自己原始的性格和真實的感受,這是最重要的。」許鞍華和黃燦然在書卷的包圍中坐下來,談詩,也談經歷。「黃燦然本身就是一首敍事詩。」許鞍華笑說。
如果你住得香港夠久,電影很多內容像是輕描淡寫,但卻能深深觸動你。像黃燦然一句「餘生只想做詩人」;像淮遠在片中誦讀其詩作:《天堂無霧—悼戴天》,短短兩句,卻黯然詮釋着當下。「你站在九龍看不見香港/五十三年後我站在香港/看不見香港」。

前幾年,在文念中執導的紀錄片《好好拍電影》,年過古稀的許鞍華已明志想拍關於香港詩人的故事,但紀錄片加詩人都難從商業市場考慮,一直膠着。沒想到天降疫情,在世界停頓之壞時刻,卻為許鞍華造就了機會。被迫慢下腳步的許鞍華,反思自己最想拍的題材,仍是腦裏縈迴了數十年的香港詩。「在我這個年紀,這隨時是我最後一部電影。」新詩在香港從非主流,許鞍華偏偏對這個題材情有獨鍾,這個心願源於那個從青年時期就寫詩、讀詩的自己。

(電影劇照)
電影和詩,一個主流一個小眾,彷彿處境不同,其實兩者也有着共有的狀態──例如時刻都在商業和藝術之間掙扎擺蕩。「精神上,你會覺得詩才是最重要的,但問題是詩賺不了錢。」自言在香港生活得被迫要「經濟流亡」到深圳的黃燦然道。「不只是賺不了錢,而且是虧本的,所以我要有一份正職來養活詩,寫一些評論、寫一些專欄,總之做甚麼都是經濟上的考慮,為了讓詩可以生存下來。」
為了在香港難以容身的「詩」,黃燦然離城而居也堅持創作,許鞍華過了數十年仍想將它拍成電影,「詩」顯然具有它的獨特魅力。

以電影尋溯寫詩的源頭
「輕一些,輕一些
──廖偉棠〈我們寫,寫不過生活〉
向生活過和正在生活的人致敬。」
紀錄片《詩》以兩個在異鄉生活的香港詩人──黃燦然和廖偉棠──的訪談為主(也有包括淮遠、飲江、鄧阿藍、馬若等香港詩人前輩的短訪,也有西西及也斯出場),他們一個灑脫出塵,一個積極入世,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態度,投射出創作所能有的各種方式。

「他們懂得平衡他們的詩和日常生活,不像我們這個世代常覺得作家就要犧牲生活、廢寢忘餐那樣悲慘。」許鞍華說,這次紀錄片特意以比她年輕的詩人訪談為主軸,是因為從他們身上看到了有別於她同代人的特質。「他們給人一種正面、實際的面貌,以及繼續生存下來的創作和生活方式。這件事對於我們拍電影的人來說,也帶來了某種啟發。」
追溯最初對詩的熱愛,許鞍華的回憶到了五歲之前:「小時候,我爺爺就一句一句、口把口的教,要我唸好五言七言。然後我五歲去了香港,他交下了《長恨歌》和《琵琶恨》,就叫我爸爸教我。我爸爸無心插柳,工作回來已經很累了,還要教我讀詩。我記得他一下班,就在外面乘涼,拿著一本書:『漢皇重色思傾國……』他每次教七句,然後我就跟着讀,《長恨歌》就是這樣練回來的。」
但原來自幼讀詩、大學時又讀文學的許鞍華,其實也隱藏了一個詩人的身份。

(電影劇照)
「那時是六十年代,我11、12歲,寫了封信去編輯部罵崑南──不知道陸離還記不記得──覺得他太無病伸吟了。我那時十幾歲,罵完又理直氣壯,自己寫了英文詩就發過去,押韻的,但我忘記寫了甚麼。然後竟然刊登了,我抱着本《中國學生周報》不敢讓別人知道,但收到稿費,不知道去買了一枝唇膏,還是請了我妹妹吃東西。」許鞍華又說,那時喜歡寫十四行詩,因為中學時讀了很多,很喜歡,寫完就發給香港大學的英文雜誌,屢獲刊登。旁邊的黃燦然聞言笑道:「其實你最初是詩人。」

(電影劇照)
還有一段經歷:讀書的時候,許鞍華的論文以美國旅歐詩人龐德(Ezra Pound,1885-1972)為研究對象,「他翻譯了中國古詩十九首及《詩經》,就想寫他、想寫翻譯的作用,覺得他的譯本比其他更好,但捱了兩年近乎情緒崩潰,最後都無做到。」
回想那時,如今許鞍華一笑置之,但那段時間寫詩的經歷,卻令她對創作有了自身的理解,也埋下了她要將詩拍成電影的決心。「很開心他們肯讓我拍,其實要誠實地分享自己對各種各樣事物的看法,不是那麼容易。當他們說肯,然後我去訪問他們時,我也不知道他們會說多少,或願意說多少。但紀錄片就是這樣,你不會知道所有東西,無法預先計劃好,而是到了現場,有甚麼就拍甚麼。」隨環境和思緒而推展,《詩》作為紀錄片,彷彿也呼應了新詩的創作形式。

窮餘生寫詩 黃燦然:詩的意義要死後才知道
「不要害怕,你無非是在黑夜裏
──黃燦然〈小伙子〉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黑夜和白天。」
九十年代在香港,寫詩的人都不敢說自己是詩人,只能默默創作;後來新詩不僅隨社會媒體而逐步走入大眾視野,到了現在,香港詩人還進一步走進大銀幕,這樣的轉變,或許標示了詩正逐漸走離邊緣。
但身兼詩人身份數十年的黃燦然說得坦白:「詩沒有甚麼現世或即時的價值,寫詩的人要有心理準備,如果你成名,或者有幾個讀者,你已經算是幸運的,如果沒有的話就是應該的。所以我覺得人生就是這樣,痛苦是應該的,快樂就是幸運,你要用這樣的心態去面對。」

以詩寫城,其實創作最終也是為了面對自己,從中感受、認識自身在不同生命階段的心態流動。「我的詩也是這樣的。譬如說在不同的階段,你會用不同的角度看自己的作品。我發現隨着年齡和你自己的感覺,它會變的。」黃燦然憶起,自己第一次讀到「俄國文學之父」普希金的作品時,覺得他的詩寫得很差,「然後過了半年再讀的時候,突然覺得很感動,並且覺得,如果我寫的詩也能像他感動我這樣感動一個人,這就已經足夠了。這個信念一直到現在都是這樣。」

銀幕前,黃燦然出塵隱居到深圳,閒時遛狗,指間常夾一根煙,看來灑脫的身影延續至日常,談詩人的自覺時,他也同樣雲淡風輕。「詩最終能不能夠留下來,這肯定是時間的作用,誰都阻止不了。當所有人都想爭取現世的名聲,但是如果你再想深一層,其實這些東西很規範,很沒有意義。一個詩人如果太注重這個的話──其實很多人很注重,我也會很注重,但問題就是,如果我沒有一條界線在那裏,那整個人就很容易膨脹。」
踏入花甲之年,近年黃燦然遷居深圳洞背村,間中翻譯或寫詩,脫離香港的高物價生活,好像才有了更多創作的空間。但詩人創作不易,問黃燦然餘生還是否要繼續做一名詩人,他側過頭看向別處,淡然笑道:「即使不寫詩,我都是一個詩人,沒有辦法。」

(電影劇照)
撰文:鄭思珩
採訪、監修:鄭天儀
攝影、剪接:古本森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請把 The Culturist 專頁選擇為「搶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