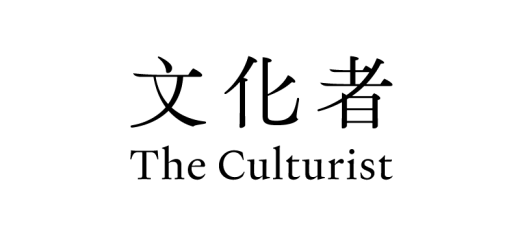「半盞清茗伴雅器,了無閑事掛心頭。」是泰華古軒主人、宋瓷收藏家麥溥泰一直夢𥧌以求的生活;與茶相許、觀自在,以一杯好茶抵抗俗世紛擾,更是他的人生哲學。廿多年前,他由一件點茶用的建盞開始了收藏大業,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在世界各地入藏的宋瓷粗略估計有六百件(套),身價千萬的藏品他也從來只買不賣,不能斷捨離。
「我收藏茶具,也是收藏一種茶的生活態度,領悟的精髓就是與人分享。」一片茶葉融宗教、哲學、倫理、美學於一體,盛器自然也融匯茶人的態度與智慧,但麥溥泰最大的感悟是:「獨樂樂不如眾樂」。

一個氣温三十度、乍雨乍晴的星期日,在調景嶺明愛白英奇專業學院,來自中、港、台、馬來西亞等的茶界專家、逾廿家本地茶單位出席了一個名為「工夫茶論壇—茶 • 工夫」的大型茶活動,最震撼的場景是超過80位年輕茶師一起泡工夫茶,最年輕的只有七歲,參加的茶友多達六七百人,營造的「茶園聚義」之景,何其壯觀。活動出錢出力的策劃人,正是麥溥泰,他希望重現宋人雅集茶會盛事,讓茶藝復興,也創造歷史。
「其實,我有想過申請入健力士世界記錄大全。」穿着一身中山裝的麥溥泰笑說。
眼前這風景是感動的,與崩緊的社會氣氛型成很大對比。偌大的空間放置了茶座、點心和茶具藏品,免費供人欣賞歇息,每位茶師泡茶方法、所用的茶具都不同,有的喜歡青花、有的拿了百多年的素杯,反映了個自的品位與喜好;大會還找來研習傳統花藝四十載的台灣花藝師林愛卿設計茶桌的花藝,觀眾隨心找喜歡的茶桌坐下,與其他茶友圍爐聊天,茶與人產生不同「化學作用」,不亦樂乎。

「工夫茶作為中國茶藝的古典流派,集合了文化精粹的一種泡茶的技法,所以各自彰顯自己的工夫,泡茶動作一個都不能少,必須專注認真。工夫茶是要看到工夫,不是自由泡。」麥溥泰呷着茶說,喝茶是輔,溝通才是真。「奉茶者與茶對像就在溝通。」
原為商人的麥溥泰,年輕時就喜歡喝茶,壯年更瘋狂愛上茶,繼而進深的了解茶的哲學、科學與美學,回溯横跨了二千年歷史的茶之本相,1997年更開始收藏茶具。原本由較易入手的明清瓷器開始,他很快就迷上更早的宋代,由茶具開始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由此,麥溥泰從各種茶葉的收藏,擴展到了宋代瓷質茶器的收藏。

「你有沒有看內地電視劇《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說的是北宋官宦家庭少女明蘭的成長、愛情、婚姻故事,藉此重塑了宋代的生活畫卷,很有趣的。」麥溥泰這位「宋癡」如是說。
蘇軾話齋:「焚香引幽步,酌茗開靜筵。」欲得閒情,先要做閒事,以閑養心。歷代將「無聊事認真做」;閑事玩得最招積、講究的,一定數宋朝。它是中國文化發展最關鍵的時期,宋人的文化趣味最濃,「燒香、點茶、掛畫、插花」成四大「閒事」。
麥溥泰沉迷看似簡約的宋代茶具,貪其多變。「南有景德鎮之湖田影青;北有耀、定州兩窑精美絕倫。」在他看來,宋代瓷器造型簡潔、流暢,一般都是單色釉,沉靜、簡淡,將瓷器的極簡美學發揮到極致。麥溥泰的藏品,孤品過半數,包括完整的晚唐定窰茶碾、北宋黑漆屈輪紋盞和托、北宋耀州窰八棱形龍首杯、北宋耀州刻花把壺連温碗等。

麥溥泰按照不同的窯口,對宋代茶器進行系統的收藏,除了官、哥、汝、定、鈞五大名窯之外,還有很多民窯,生活器風格更自由、隨意、多變,包括耀州窯、磁州窯、建窯等。他周遊列國、從不同拍賣會或私人藏家手上,尋找各窯口的名品,當中的患得患失又刺激又忐忑。
麥溥泰把他得意收藏逐件曬冷,其中一件「汝窯天青釉盤」就意義重大,是他在夏門一個拍賣會投得。「宋代大小窯子,包括五大名窯的器物我都收齊了,獨欠第一名的汝窯,這藏品完滿了我的所藏,所以對我而言是關鍵之物。」
他收藏了一件北宋定窯黑釉醬彩盞也非常難得。定窯主要生產白釉,但因為宋代流行鬥茶,所以當時定窯也生產了一些黑釉盞。這件黑定醬彩盞上還有描金特別珍貴,日本茶道界將這種黑定當國寶來看待。
另外一個「宋代天青釉汝窯八仙酒瓶」上面畫了八個仙人,麥溥泰從日本入藏,他說茶壺看到了古人用了幾百年的痕跡,保留了傳承有序的故事。配以宋代青釉素杯和明清的漆器茶座,幻想着宋人的風騷。
魏晉南北朝時差文化的創立期,唐朝茶聖陸羽的《茶經》問世,把喝茶推到藝術層面,宋代進入了黃金時期,品茗甚至成為一種精神修煉的茶道,傳入了各種用茶的方法、及衍生與茶有關的宋器物。他說一件上乘的茶壺,既能將茶的韻味發揮得淋漓盡致,亦具收藏觀賞價值,更有歷史意義,好玩、好研。得到心愛之物後,他做研究、照相、做盒、到搜資料、做研究、事必躬親,樂此不疲。
記得多年前認識麥溥泰時,我們是由聊茶具的一分鐘朋友開始。在一個學術交流會,他從上鎖的飾櫃小心翼翼的拿出一套日本江戶時期的古董組合茶具,跟我分享。這旅行式茶具套裝有小銅爐、精緻的茶壺、茶葉小匙、精工的茶杯。
「古時日本人就是帶着這種茶具到郊外野餐品茶的,把炭放進小銅爐起火,一家人喝着茶閒話家常,多愜意,茶有濃厚的人文精神。」他細心地逐一工序解釋,手工輕輕地把玩着茶具,我腦海不斷想像古時草地上優雅地喝着茶的一家大細。
他再展示寶貝,一隻非常優雅的宋代八角型的酒杯配鐵底。「八角款是獨一無二,不能拉杯,要用手慢慢捏造,這也是在日本收回來。」

麥溥泰說,在宋代,飲用茶主要分煎茶和點茶:煎茶的具體做法,是在風爐上煮水,待水微沸,將茶末投入水中煎煮攪動,然後斟入碗中飲用;點茶則是先取茶末在茶盞中調膏,然後用滾水沖點。煎茶多用於二三知己的小聚與清談,點茶多用於宴會,包括家宴,也包括多人的雅集。因此,對宋人來說煎茶蘊含的古意特別為文人士大夫所重視,而點茶引發的鬥茶是兩宋茶事中的盛事。

「一人品茶得神、二人得味、三人得趣;更多人對酌,自可得樂。」麥溥泰認為,收藏原是很個人的事,但他卻希望把茶文化推廣。「柴米油鹽醬醋茶」是開門七件事,表明居常飲茶是一種生活方式,老百姓不可一日無茶,以茶養生、以茶悟道、以茶會友,像外國人喝咖啡一樣普及。
廿多年來,麥溥泰從最初的茶葉、宋代茶器的收藏,漸漸建立起一個以還原宋人「四閒」為主線的龐大收藏體系。2016年,他更於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內舉辦名為「閒事與雅器」展覽,280餘件展品均是麥溥泰的私人藏品。
時代上起唐代,下迄明代,以宋代(包括北宋、南宋和金代)為大宗。品類以瓷器為主,輔以金、銀、等;又以茶、酒器為重,兼及花器、香器、文具。力圖按器物的使用功能,細分不同的器物品類,使觀眾可以從不同的層面深入了解宋人的文化生活、用器之道和器藝本身。更有趣是,對於前來參觀的好友,麥溥泰都會親手奉上一杯他珍藏的好茶,展品中數量最多的就是宋代的茶器。


這次展覽在行內引起哄動,他還特別設計了煎茶具、點茶具、酒器、香具和花器五個專題情境展示。他又花了逾四年時間,出版了《閒事與雅器》一套三冊的精裝書,談宋代清雅藝術的閒事風流。他除了找專家、考古研究院的博士生替他為每件器物寫研究文章外,更特意找來最好的器物線圖繪圖師替他勾畫線圖,非常嚴謹。
「宋朝的文化必須傳承,不能忽略當下。宋文化一樣的影響日本,還影響歐美的早餐茶,所以它應該有當代性。」麥溥泰托情寄意,流露着宋人的風格品貌,他的心願是將自己的心得傳承下去,讓更多年青人了解宋人生活態度。

採訪、撰文:鄭天儀
攝影:余日一、鄭天儀
(原文刊於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