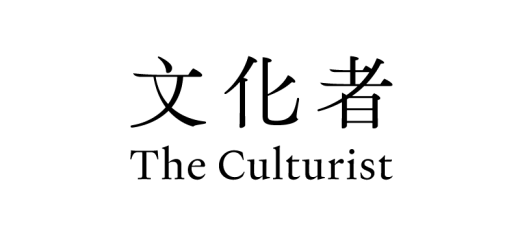《敦煌》展覽又來香港。
過去兩次展覽,2014年的《敦煌―說不完的故事》有一尊近13米長的臨摹涅槃佛像,磅礡大氣,展覽用上五大展廳;2018年的《數碼敦煌——天上人間的故事》,重現3大敦煌石窟,展覽用上VR,也用上了造像,記得當年有個由香港知專學院設計的《勞度叉鬥聖變》,以遊戲形式展示6場戰鬥法,夠貼地而且創新——文科生總希望有日可以「耶穌戰佛祖」,「鬥聖變」某程度上實現了這個也許是男生才會有的妙想。
2019年後,換了人間,《敦煌》展覽第三度來港,《敦煌―千載情緣故事》主力重現建於中唐時期的榆林窟第25窟複製洞窟,以及展出敦煌文物,包括一批1900年在第17窟被發現的7至10世紀的遺畫;另一展館則主要介紹同樣出自第17窟的絹本佛畫「報父母恩重經變」,將《盂蘭盆經》中的「目連救母」本生故事,透過投影呈現。展覽今天要我們「尊天」、「敬地」和「愛人」。

《敦煌》的展覽都是好的,展品的歷史底蘊源於遙遠憧憬之地,西域與中原要地的風沙,隨歲月更迭,窈冥撲來。照見飛沙之間,全靠一代代人,無論處於甚麼時局,都尊之敬之歷史文明,靠他們的一雙眼,一雙手,把使命執著起來。
敦煌有盛有衰,古往今來都是搖搖欲墜的邊疆城市,騎兵馳騁之所,終年吹刮黑沙暴,氣候溫差很大,最高44.1度,入夜最低零下22.6度。西漢初漠北匈奴佔領敦煌,漢武帝時出兵鑿通西域,敦煌易主,設敦煌、酒泉、張掖、武威四郡,敦煌郡立,敦煌因與西域通商而盛,當時人口三萬多。南北朝時期,北魏延興四年(474),北魏朝庭打算放棄敦煌,將百姓遷走,此時出身官宦世家的韓秀力排眾議,堅決反對,認為百姓不能退,他也成為了拯救敦煌的人。敦煌最盛在晚唐,然而元明時已衰微,清朝雍正立敦煌縣,修整一番,但「寺已久湮」,「畫留人不留」,客觀環境已難比盛唐。
據說上世紀60年代以前的敦煌石窟沒燈沒電,研究人員得靠鏡面反射,加上入夜深寒,研究環境非常艱苦,留居要有覺悟。大家可讀讀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的自述便略知一二,她寫道,當她在北大歷史系畢業後被分派去敦煌「就業」後,父親寫了封很厚的信給她,囑咐轉呈領導婉拒分配,她思慮過後並沒有交出,該信在「文革」期間,連同其他信件一併燒毀。種種原因,她事業在敦煌,心歸敦煌。
平日研究人員主要從事臨摹與保護,因為壁畫會有「病」,小則色彩變黑,大則脫落,石窟結構也須加固,修復年復一年,永無止境;修復,然後是「敦煌學」,探索文明意義史。修復進度常受時局左右,例如1962年周思來下令大規模修復石窟,石窟修復漸入佳境,但到十年「文革」,修復壁畫又成了大罪,石窟墜入幽暗微光。這些都是歷史,鐵錚錚的,敦煌在幾經波折而又能存活下來的,都是好的,所以展覽來了,敦煌能存多少,我們能看多少,就看多少。
今天香港人都經過歲月洗禮了,我總覺得,「尊天」、「敬地」和「愛人」,總是對的。是次重點展品榆林窟,是一壁一經,南壁是《觀無量壽經變》,《觀無量壽經》是「淨土三經」之一,呈現時人信仰,對西方極樂淨土的想像,再透過「經變」(以繪畫藝術去表達經書的一種藝術形式)畫出更見靈活。古往今來世上之人對極樂淨土,都有著不同的想念,天地風雲再變色,我們都持守著一份嚮往,天地之間,或者六合之外,嚮往就是對的。日本京都平等院的鳳翔館所藏的《當麻曼荼羅》,就呈現了日本天平宝字時代的阿彌陀淨土,而榆林窟的南壁的《觀無量壽經變》,就呈現了滲入吐蕃的淨土想像,屬於那個時代的嚮往,這部分建議細看,把「極樂」深印腦海,沉澱出屬於我們的極樂。

莫高窟第172窟 南壁
盛唐
敦煌研究院提供
(圖片來源:香港文化博物館)
與前兩次相比,今次整體精緻唯美,偏重美學包裝貫穿主題,剖析壁畫中的經典山水場景一隅也很有趣。我對50厘米高的盛唐木雕坐佛像以及敦煌遺畫《降魔成道圖》比較有感。坐佛像形態「人物豐濃,肌勝於骨」,令我回想有年到日本信樂的MIHO美術館,看過的一個紫香樂宮(日本奈良時代聖武天皇的離宮)展覽,那尊木造十一面觀音立像,和那尊藥師如來立像,都是「肌勝於骨」,那年還能無憂無慮出國旅遊,安逸的泡沫,還未被戳破。
《降魔成道圖》在第254窟南壁就有一幅,而今次展覽的《降魔成道圖》是一幅絹畫。時代不同,特首不同,但天地正道,人魔殊途,釋迦結跏跌坐,降魔印不會不同,我想再看看,魔眾人物,到底是甚麼個模樣。

今次展覽,大家別漏看展廳外面的第148窟《藥師經變》,以及《觀無量壽經》之「未生怨」和「十六觀」,《藥師經變》像一般展板,若改放到展廳當中,效果或者更佳;展場內《九色鹿》的本生故事部分也最好先備備課,跟子女講解,由於現場缺乏指引,沒有短片故事(也不一定要放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的版本那麼長),裝置本身也沒有任何互動元素,見有孩童騎在九色鹿的裝置上被工作人員斥責,各家長宜看管好,否則孩童會提早體驗「因果報應」。至於敦煌遺畫的電子教學板「古絹解密」,程式時有反應不來,多按兩次便是了。
說回「目連救母」,是說釋迦牟尼佛十大弟子之一「神通第一」目犍連尊者,他的母親在世時做了不少壞事,死後墮進餓鬼道,目連運用法力給母親送飯,飯未入口就化灰了,目犍連非常傷心,於是向佛陀請示解救之法,其母最後往生天界,出離地獄昇天。如果你的「母親」,做盡壞事下了地獄,你還有沒有勇氣去愛?或者大家試試在展廳當中,踏著光影生出的虛幻之花中尋找答案。
「愛人」是否真的要「目連救母」呢?如若「目連救母」是主旋律,你又當如何?我以為,愛人不如愛己。或者是我缺慧根,愚頓,不理解目犍連。
看完展覽後,對自己好一點,生出文化旅遊念頭,遨遊天地間,不也是好?或者像常書鴻因讀到伯希和寫的《敦煌千佛洞》而決志投身敦煌事業一樣,踏出展廳,就去尋訪佛像佛畫學問之堂奧,看看梁思成說的唐代最上品琉璃瓦塑羅漢的真容,也是愛己愛人,於人生也是一種福氣。

撰文:佟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