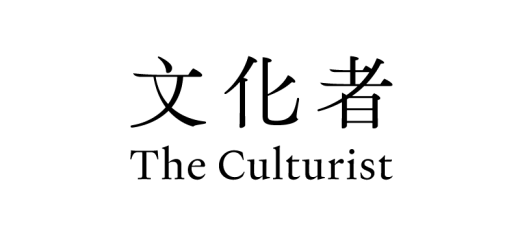「《圍城》入面我對城寨最大的感覺是一處『離不開、留不低』的地方,看似無情這亦是城寨的美麗。它不是要你留低、亦毋須當呢度係你個家,從來它都是一個俾你唞啖氣、回過神,再返出去的地方。」—— 導演鄭保瑞
反差感製造人格魅力。
那天,在出爐金像奬「最佳導演」鄭保瑞的工作室專訪後閒聊之間,他失驚無神端出吸塵機來吸塵,但其工作室已近乎一塵不染、書櫃井然有序像圖書館。「挑!難道拍《智齒》我屋企就似垃圾崗咩?!我個人好有條理㗎。」他顯然從我臉上讀到疑問,急不及待狡黠地笑着回應,配樂是吸塵機聲的嗡嗡聲。
這種反差,也出現於瑞導的新戲《九龍城寨之圍城》(簡稱《圍城》)。
鄭保瑞自小從澳門移居香港,19歲進入電影圈由低做起,像海綿般吸收林嶺東、劉偉強、馬偉豪、葉偉信、杜琪峯等香港著名導演的精華,廿年前首執導演筒乍洩暗黑變態偏鋒,到《智齒》與《命案》達爐火純青的重口味,以「活著比死亡更無能為力」的視覺震懾觀眾。這次罪惡之城、黑幫故事揸手,合曬鄭保瑞工尺,還不肆意將暴力美學進行到底?偏偏,《圍城》拍出了很不瑞導式的陽光感、混雜汗臭與本土回憶的麻甩佬浪漫。
「我們做了很多研究,不只是城寨的資料搜集,還有那個年代的資料搜集,怎樣講一個原本比較黑暗的故事?後來,我們決定把主角洛軍身份改為一個難民,走進城寨的經歷,再慢慢審視這個世界。」瑞導娓娓而談。

城城:「最懂折磨演員的導演」
郭富城在說鄭保瑞最懂得發掘及折磨演員,發掘是呈現演員最優秀一面;折磨是逼演員變到自己不認得自己。看完試片,驚喜位正是瑞導把林峯由大台「花瓶」變成有血有肉的打星,還被洪金寶盛讚「搣甩花拳繡腿」。「其實我覺得阿峯他自己很有心去準備改變。大家都知道我是什麼人(在垃圾堆拍完《智齒》劉雅瑟笑指有創傷後遣症),早已有心理準備,哈哈。林峯是個很聰明的演員,我告訴他是一個難民,跑到街上不知自己要去哪的那種無助狀態,他那個那個茫然不知所措的表情演得很好。」
大概8年前,陳羅超游說鄭保瑞執導《圍城》的過程也頗戲劇化。「他擔心不是拍城寨的實際難度,而是怕故事不是我喜歡的。他請我用自己方法修改,或者與作者談判一下,彼此磨合試試看。」瑞導邊回憶邊笑說。
這也是小說作者余兒曾經憂慮的,怕瑞導簽名式黑暗蓋過自己的故事初衷。余兒劃好底線:主角身份、故事、講故方法可以改,但角色與人物的關係不能。「這個我絕對贊同。如果連關係都變了,其實沒有需要改編這個故事。好看的是譬如這幾兄弟的情誼、龍捲風的神秘與經歷。」創作人惺惺相惜,所以《圍城》你會看到不一樣的鄭保瑞。

城寨記憶:神秘又有型
未接拍《圍城》之前,瑞導對城寨的感覺處於很片面的普羅幻想。記得小時候一次巴士急煞掣,姐姐沒站穩撞崩了門牙,母親立刻帶她去城寨找牙醫,這是他唯一的城寨記憶。然後是一些電影《省港奇兵》、《追龍》等,把城寨拍得像一座恐怖城。
「聽人說城寨的故事,小時候一定害怕;但王家衛的《阿飛正傳》也在城寨取景。」記得扮演賭徒的梁朝偉嗎?電影末段他整裝出門前待在那個狹小的閣樓?不就在傳奇的城寨。對鄭保瑞而言,城寨既神秘又有型;邪惡又浪漫。
勇字當頭,鄭保瑞也不是無所畏縮的,他認真考慮了兩、三個月,才決定接拍這高難度之作。
果然,導演筒執起,大小問題像雪花飄來,鑊鑊新鮮,漫長的立項審批之外,最大的衝擊自然是世紀疫情。
「本來我們已睇好景,在佛山找到荒廢建築搭建城寨,因為那邊的工程費較便宜。疫情來襲,我們唯有把整個陣營轉移香港去。此舉引發更大難題,物料、人工甚麼都貴,但錢不會因為你回港而加碼,我們只能在同一個資源裡面做到最好。」瑞導回憶這單不可能的任務,眉頭不免緊皺一下。

但「無中生有」從來是香港電影的核心價值,電影人就是有本事「蕉渣價造出燒鵝味」。鄭保瑞當年便以8萬8港元拍出處男作《第一百日》,拍恐怖片《大頭怪嬰》亦因無錢而決定道具怪嬰缺席,氣氛搭救,他坦言香港電影人慣了無資源而各出法寶尋找自己的味道。
拍攝過程也迂迴曲折,疫情來勢洶洶殺劇組一個措手不及。「整個美術組逐個逐個倒了,全軍覆沒。然後又到服裝及其他組別,我好運最後都沒中招。」
塞翁失馬,香港故事香港拍,自然原汁原味更有質感;而疫下空城,讓攝製團隊能拍出平日求之不得的鏡頭。「我們不需要用電腦特技做一條廣東道,而真的能在清晨七八點,在無人的廣東道取景、九點在彌敦道追巴士。」
這次,還原九龍城寨,成了美術總監麥國強的肩上重擔,他就是鄭氏另一話題電影《智齒》中,把一個架空髒亂的人間煉獄搭建出來的魔術師。
豪擲幾千萬、三個地方搭建的九龍城寨實景,加上高端特技展現低端人生(high tech and low life),碰撞出不只是港式頹廢型 Cyberpunk。「想現實得來帶點夢幻、科幻中間又夾雜點港漫的感覺,最重要是城寨那陣『除』要夠濃,按我們的標準。」瑞導說。
在實景中還原城寨的龍蛇混雜,鄭保瑞強調適可而止的克制。「城寨肯定是骯髒和亂,但我們沒有放大這種骯髒,和《智齒》隔着銀幕都感到臭的狀況不同。麥國強展現城寨的亂中有序的迷宮效果:外人不懂走進去,但城寨人卻識途找秘道,左穿右插回到家的實況。」
男人的汗臭與鼓油味
鄭保瑞透露,為了拍攝效果,《圍城》場景地下的水窞裡並非污水,而是黑漆漆的鼓油,整個片場洋溢男人汗臭與濃濃鼓油味。「完好的地我們特意把它鑿爛,希望可以保留到城寨的生態。當然我們好想復刻城寨建築的岩巉與不規則,路上無端有半個平台、窄巷盡頭是道門,但每項工程都是錢,而拍攝上用不着。」
因為《圍城》的城寨實景分佈香港三個地方,是個空間大挑戰。鄭保瑞說像在介紹高科技產品般興奮:「其實整個戲有多達80個場景,需要很多不同的位置去拍攝,因為資源很少所以整個城寨要模組化,像lego般組裝,每個場景都裝上滾輪讓它自由組合,瞬間就可以變成另一個景點,今日是天台、明日是樓下,這是一個無中生有的破格。」
這讓我想起加拿大劇場大師Robert Lepage的舞台魔法,瑞導卻指妙計乃效發自香港鬼才導演徐克當年拍《刀》時候所用的貨櫃場景。「他找來多個貨櫃變成不同場景,接着不停變陣,我們也就挪用概念。但執行起來相當困難,因為兩三層高的牆十分重,移動時要做很多測試。」
正因為場景不斷移動變陣,郁動了就無法連戲,所以拍攝期間要特別謹慎,「換了場景就無得補拍,這是最痛苦的事。」
自小在城寨長大的林家棟,成了瑞導的首位顧問與環境指導。「家棟小時候在城寨住上十年八載,恰巧是電影取材的八十年代;杜sir杜琪峰也住過城寨,但年代早一點。」《圍城》監製莊澄也在城寨出身,自然也成為鄭保瑞的軍師,脫口問對方:何故要住進城寨?
莊澄回說:外面生活成本高,窮人進去是找生活,因為外面找不到。「那城寨人是不是要一世在圍城生根?他們其實想走,不希望下一代住在這裡。怎樣才可以衝出去呢?就是在這裡好好生活、賺夠錢,抽身離開。」

「拍談情說愛的戲我就流汗」
城寨是香港殖民地時期,一座由居民獨立自治的圍城。瑞導指,城寨是港人重要的集體回憶,故希望《圍城》能摻雜本地歷史,讓角色與香港的命運緊扣,例如把主角洛軍安排為難民。
自覺拍氣氛電影比較手到拿來,瑞導自認最難拿捏的,是拍出主角四人的兄弟情深厚而不肉麻。「我對拍情感戲是很害怕的,拍談情說愛的戲我就流汗,尤其是男人,我不太懂得處理,總覺得多一點就老土,另一監製葉偉信在這方面給予我很大的啟發與幫助,他總是能在細緻位打動人。」
苦燉8年,《圍城》終於見天地,此經歷對鄭保瑞影響甚深,令自小在深水埗長大的他,對香港市井風景的體會完全改觀。
「大家受電影情節影響,覺得城寨就是三不管、黃賭毒、無法無天的罪惡之城。但是我看了許多書和資料,又跟曾住在裡面的街坊聊天,慢慢你會覺得八十年代未必是這樣。我很喜歡小說描述的那個城寨,是一處『離不開、留不低』的地方,看似無情這亦是城寨的美麗。它不是要你留低、亦毋須當呢度係你個家,從來它都是一個俾你唞啖氣、回過神,再返出去的地方。」這是鄭保瑞最大的感覺,正是戲中龍捲風對洛軍說的一席真心話。
鄭保瑞說,劇情上主角是重要,但宏觀地回看城寨,其實一班小人物才是城寨主要的構成元素。所以《圍城》片尾的彩蛋,攝製隊決定找來許多真實的小店人物粉墨登場,讓觀眾重温香港的生活温度。
「城寨以前有許多舖頭,有造麵、包餃子、補鞋、串膠花、賣煙仔,還有許多技術型工種,我們找來真正的師傅回來拍他們的工作片段,魚蛋姐姐、補鞋伯伯……我是越來越珍惜這些人,與他們的生活面貌。」
翻查歷史背景,城寨本來就是個歷史遺留下來的臨時圍城,它部分建築物甚至沒有打地基(因為建築物太密集,互相支撐着所以沒有崩塌)。復刻一個比城寨更臨時的場景,對鄭保瑞與麥國強而言,有一種「短暫永恒」的雙重諷刺。
正因《圍城》前期後期創作都是一個大工程,當《圍城》煞科前夕,搭建的街道、建築物就要被堆土機拆卸移平,鄭保瑞想出了一個主意。
「明天就推倒了,我請攝製隊今日就拍街,他們問拍甚麼?我說:『拍空鏡!』他們就順着整條街、所有場景,留影。哪怕是一張垃圾蟲的海報、手寫招牌、標語、士多裡的汽水機等等,我都覺得有它的時代價值,好想純粹記錄那一刻。」因為年代久遠,《圍城》許多道具,都由美術團隊親手造出來,鄭保瑞想記錄這份難能可得的價值與質感。
他傾之於心的,是圍城內、香港那些年一枱一櫈一紙一瓦爆裂開來,堅韌而璀璨的草根色彩。

採訪、撰文:鄭天儀
攝影、剪接:古本森
劇照由無限動力提供
城寨專訪系列:
【城寨專訪系列1】「最佳導演」鄭保瑞 暴力中的陽光 暗黑圍城「離不開、留不低」
【城寨專訪系列2】野性城寨 建築像植物延綿生長 余兒:壞時局仍有生機的故事
【城寨專訪系列3】八年抗戰的幕後推手 莊澄:城寨記憶是重要資產
【城寨專訪系列 4】還原城寨移動城堡 另一夢幻「big 貴完」麥國強:「拆景時像失去一個家」
【城寨專訪系列 5】建一座鉅細無遺的圍城 「城寨四少」:拍電影是成就一個夢
【城寨專訪系列 6】漫畫迷死咬不放的堅持 陳羅超:我信香港電影未死!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請把文化者 The Culturist專頁選擇為「搶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