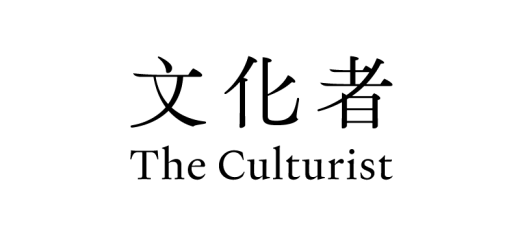一句道歉係咪咁重要?係,真係好重要。至少繼《翠絲》三年後帶來第二部長片《濁水漂流》的導演李駿碩(Jun)是這樣想的,而抱持相同想法的觀眾也報以行動支持,讓電影票房在上映三週內破500萬。
選擇從街友群體入手建構故事,電影內幾乎每句粗口橫飛的對白都能成為社交媒體的status。有人說Jun行得好前,在今日唔知聽日事的電影工業裏,仍願意透過「議題電影」為相信的價值「直斥其非」。作品彷彿被視為反抗的象徵,身為創作者的Jun卻謙稱沒那麼偉大,更不會期望電影能推動觀眾去做些甚麼:「其實我完全不是以這樣的出發點去想這件事。」他說,故事要呈現或表達的,其實很純粹:「主角一行人遇上一件要追討的事,過程裏慢慢有人放棄、屈服,甚至選擇離開,然後迫不得已地需要面對一個追求不到的狀態。」
無力感、灰心、妥協…… 有沒有很熟悉的感覺?「作為一個人,這是很基本的狀態;無論你是否『有瓦遮頭』、街友甚至性小眾,你都能理解到的、一個關於人性的狀態。」

怒火衍生的故事
「這本就是一件令我很憤怒的事。」2012年2月15日,情人節的餘溫沒有遍及城市每寸角落———— 包括深水埗通州街天橋底下40多名街友。因為他們的被鋪、保暖衣物甚至金錢和身分證等個人物資,在沒被事先通知或查詢的情況下,全被政府當成垃圾丟掉。當時作為中大學生記者的Jun大感震驚,遂為此事寫了篇報導:「2012年左右,當時街友們都還是席地而睡的。在深水埗玉石市場的牌匾底下,很簡單一個床位,個人物品、家當就放在旁邊。而不同街友群體雖有各自的生活,但被外人來訪也很隨性、對外界的攀談也很歡迎……」

即使發生過該次清場事件,他觀察到街友們對世界其實無甚敵意:「但往後幾年,繼續發生不停的驅趕和清場,始終逼使他們在生活上作出改變——起木屋。雖沒那麼容易被趕,但同時對世界築起了圍板,孤立自己,或許連街友也互相不知道對方在屋裏發生的事。」越發濃烈的惡意,讓街友在物理和心理上同樣被逼成為封閉的群體。彷彿感到切膚之痛,在2017年左右重返通州街天橋底的Jun看着一間間木屋,勾起想要想寫劇本的衝動:「決定下筆的時候,正值政府慢慢清場的時期;寫完的時候,場地就完全被清空了,我看到了一個通州街橋底完整的變遷過程。」Jun淡然道。曾是深水埗街友代名詞的通州街橋底,在2019年左右被清空。與各區多個被視為街友落腳點的天橋底空間遭遇同樣命運,現已成社區裏一個個被鐵絲網重重包圍、空置而孤立的空間。
「有些情緒是與拍攝當下共通」
故地發生巨變,同年發生的社會運動亦為整個香港投下一顆震撼彈。劇組卻選擇在十月底、風頭火勢之時正式開機:「8月時感覺上還很激烈,9月好像靜了點;10月的時候有種『現在不拍就沒機會了』的覺悟,所以就開機了。誰知11月才是最激烈的月份…..」淹沒在催淚城市中,Jun坦言當時狀態「好艱難」,曾掙扎過是否繼續;至11月中期,終在深水埗區內一處經挑選過的天橋底空間搭好了木屋群景:「『返唔到轉頭』了嘛,唯有硬着頭皮拍完。11月中旬有幾天是開不了機的,還好能趕及11月底前拍完,避過了後來的疫情。」Jun坦言「有些情緒是與拍攝當下共通」,讓我好奇搭配着如此鮮明貼地的故事主題和拍攝地點,過程中會否有像拍紀錄片的感覺。他斬釘截鐵說沒有:「這始終是一部劇情片啊。因為我在拍一個與我當下身處不同時空的故事。只是鏡頭運用、各項美術和美學上的處理手法跟紀錄片相似,均以一個最近似真實的狀況為依歸。」以2012年清場事件為起點,輔以幾年來對街友群體的觀察,Jun下筆寫成一群街友為自己走上一整年維權路的故事。

「這是一齣以劇情推進的電影,只是非誇張於現實、高潮迭起的那種劇情。戲內各種關係的轉變,就是由各種生活上的小事,環環相扣而成。」Jun憶述2019年清場後,街友被迫四散到不同地方,各自重組全新的居住環境:「例如隔壁通州街公園裏面,或者走遠點、李鄭屋邨球場的看台上面…… 但已經不再是同樣的生活節奏,人際關係也改變。」何處為家,何者為鄰?街友在流動的狀態裏過活,與無常並存,離合散聚即日常。戲內有人上樓,有人留守街頭;面對同屋的離世,有人哭崩,有人卻只視空出了的床位為歡迎新住客的見面禮…… 互相依靠、廝磨、傷害,戲內街友群體看似平凡的日常生活,共同產生看似微小的決定,都赤裸地展現人能有多善良、邪惡、偏執、脆弱:「概括一點來說,這齣電影就是希望呈現不同的人性特質。」

「我哋老同係咪好X恰啲?」
「我覺得一句道歉很重要啊。」就無理清場事件,戲內的街友們在社工何姑娘帶領下,透過社區組織跟政府對簿公堂。對方開出的條件是賠償2000大元,但不會向街友道歉;假若堅持要對方道歉而不肯庭外和解,很大機會影響裁判結果,最後可能兩者均到不了街友手中,得不償失。接受就皆大歡喜、不接受就一個累街坊。戲內的大眼輝周旋於自己的倔強和同伴的壓力,是群體內唯一堅持不接受對方條件的人;雙方自然產生磨擦,然而在司法制度的高牆下,其實大家都是苦主:「輝哥其實講得好明白了,他的立場不是說不要錢而只要道歉。他是問,甚麼是賠償但不道歉、這些錢又代表甚麼意義?」Jun有很多疑問,他不解如果對方不覺得自己有錯,那為何要賠償?如果道歉這個動作,會令政府往後執行清場工作產生難度,是否連賠償這個貌似承認自己做錯的動作也不應該提出?何以要在語言藝術上周旋?接連拋出疑問,Jun吸口氣續道:「(賠償的用意)明明就是承認做錯了,而你卻總不肯說出口。所以那一句道歉就變得更重要了,這是我的立場。」

「一句道歉是否真的很重要?」這道在戲內常出現的問題,本來就十分重要,因為其同時隱含着人與人之間價值觀上的差異,也正是Jun希望探討的人性面向。在前作《翠絲》談跨性別群體、新作《濁水漂流》談街友,兩者均總是被標籤為主流以外的「邊緣」群體。題材與觀眾之間,總存在着曖昧的距離:「拍這兩套電影的時候,我常常思考,甚麼是『我』或者『我們』和『他們』;我會從觀眾的角度去想,基於甚麼原因而讓他們能代入電影裏的角色。」電影裏上一幕仆心仆命為街友付出,下一幕就回到豪華自宅、擁中產背景的社工何姑娘;諷刺地道出資本主義下貌似受益者(同時也是受害者)如我們,不論多想努力提供支援,總無法真正理解社經地位較自己低的持分者的需求。始終不能否認,「我」/「我們」與「他們」,總有着一道難以跨越的鴻溝:「我們該如何跨越隔閡?就算無法跨越,我們又能如何誠實地面對這個距離?」他給出很基本而老生常談的答案——同理心:「到電影(《濁》)的結尾,我就想,其實憤怒就是一種可以共情共理的進路…… 不需要任何原因,我只要知道他對這件事(街友被無故清場)同樣表達憤怒的反應,其實我已經可以跟他一起走在這條故事線上。」
「所有事情對就是對、錯就是錯,黑白分明?」我問。不愛凡事「畫出腸」的Jun點頭、輕聲回應。

這也是他何以冒着被觀眾批評敘事有欠完整的風險,仍要抽走/選擇性交代角色背景的原因——觀眾是否會因為對人的道德判斷先入為主,而放棄相信眼前看到的不公義,Jun希望透過電影尋找到答案:「舉個例子,觀眾也許很容易會認為『老同』(吸毒者)就是『自己攞嚟』,而拉遠能同理街友的距離和可能性。」他強調並非每區街友皆為吸毒者。然而這個從主觀角度出發的故事,正是發想自深水埗通州街橋底—— 一個在Jun眼中、明確地有很多街友吸毒的地方。假如拿走吸毒元素,就是對真實的不尊重:「不會為了令角色討好點,去講一個輕視街友群體真實性、而令觀眾同情的故事。反正我的信念就是,一個人從哪來、有着怎樣的身份背景甚至染上毒癮之類的惡習也好,也有捍衛自己尊嚴的權利。」這是Jun當下對公平、平等、正義、人權等概念的認知。
直視傷口
「然而,我並非希望『你看完戲之後去關心一下身邊的人』或者『去解決那個議題』,這叫慈善。在一個更大的制度底下,例如土地問題或更多類似這種如斯困難的矛盾,是無法以善意解決的。我們沒人能解決到。」Jun多次強調無意把作品形塑成說教式的「議題電影」,連飾演輝哥的吳震宇也曾直言「拍戲唔係要你同情一啲嘢」。電影裏的街友被各界來訪兼消費一番,虛無的同情心最後還是沒有為該場官司或街友的生活產生任何改變;已上樓的街友減少回到街頭、吸毒的繼續顛沛流離、逝去的則不復返,繼續各自過活如常。電影最後以分鐘計長燒的一把火卻告訴觀眾,我們實質上正步向毀滅:「有時,我們不得不面對很多絕望的狀態。」Jun很坦白,這就是一齣逼觀眾卸下偽裝,直視現實的電影。
在戲中多年前送走妻兒、因自己犯事而無法共赴挪威的越南難民「老爺」,與兒子在網上相認後選擇結束生命。是否淪落街頭的「老爺」無法面對活得比自己好的兒子?Jun不同意:「他就是很期待一件事情(與家人相聚),這件事是他在世時唯一願望;然後終於等到了,他也就達成了自己的心願……」Jun不希望說得太明白:「但對我來說,(『老爺』自盡)不是一件逃避現實的事。」誠實直面曾經是自己人生的遺憾和傷疤,「老爺」大概比更多人還要對自己人生負責任、勇敢。

「所以我覺得電影不是作為我們苦澀人生的一個慰藉,因為銀幕是一面鏡子。也就是,觀眾能在故事裏面反照到自己的甚麼面向。」電影明確地告訴我們,時代和世界就是崩壞得讓人如此絕望;集體直面絕望,未必保證能打開希望的缺口。至少在必然通向毀滅的過程裏,我們還有彼此:「代入了那種情緒,是憤怒又好、旁觀他人痛苦而感受到痛苦也好,那其實是電影裏面給你,也是生活上真實賦予你的情緒。這齣電影就是一個記住了當下、集體情緒的一個紀錄。」
在朝不保夕、事實也能被任意竄改的時代,所幸電影仍能作為證明某些人、某些情緒真實存在過的記錄。即使肉身最後要步進遭焚燒殆盡的命運,信念仍能隨作品永久封存。

撰文:熊天賜
攝影:陳昶達、熊天賜
剪接:陳昶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