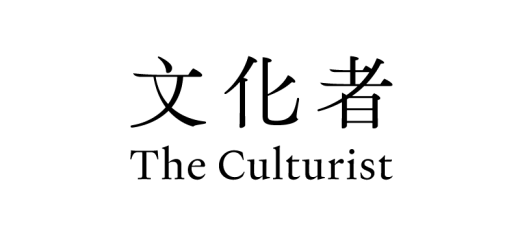「我們以藝術的方式將這告訴大眾:生活是多元的,而且離不開真善美。我們可能有很多話想說而不得,但我們的悲傷是真切的。」
——香港編舞、舞者兼攝影師曾景輝

當毛髮鋪天蓋地、黏液在數具身體之間糾纏欲滴,在編舞曾景輝(Terry)與創作團隊的鏡頭下,與身軀私密部分一併被放大的,還有潛伏人心的恐懼。
近年疫情改變藝術生態,無法在現場出演的節目就以鏡頭攝錄下來,移師網上放映,但對於涉獵舞蹈攝影多年的Terry來說,鏡頭早已超出功用性的「記錄」作用,它本身也擔當着舞蹈員的角色,既能凝定於一瞬,也能將觀眾帶到表演者的身旁,化成主觀視角,在整個空間的各個角落四處游移。
在錄像藝術氾濫的當下,Terry結合編舞、舞者與攝影師的多重身份,遊走肢體、色彩、道具和空間所構成的視覺衝擊,將鏡頭指向近年的經歷。在其一連四集的實驗性錄像作品《景 · 色》中,邀請了兩位導演——楊適榕(Kitty)和吳欣堂(Rose),聯同創作團隊的多位成員,從個人對毛髮的私密恐懼,推展至外在的家庭關係及創作環境,最終探討人與自然的關係。

在這一系列的作品中,不論是懸吊在劇場上空的軀體,還是在旺角鬧市中行走、引來途人側目的鬼魅生物,都一再挑戰着我們慣常的觀看方式。創作人將自身的恐懼置於鏡頭前審視,作為觀眾的我們彷彿也在視聽的衝擊下被敲問,從而反觀自身在不同語境下的壓力與恐慌。鏡頭和舞者的身體重新為美學定義,將既定的觀看方式加以扭曲和重整過後,能否撇下外在的掩飾,以原始的慾望和美學,作為對繁複世界的回應?
從鏡頭反觀舞蹈 視覺衝擊的新可能
全職專業舞者出身的Terry,與很多劇場表演者一樣,最初是以舞台作為主要的表演平台。在排練室裏不斷練舞、排舞,數年之後,他忽然希望探索身體以外的媒介,便毅然買了部相機,甚麼攝影基礎也沒有,在街上隨意捕捉各種人像與景物,沒想到就此對攝影深感着迷。用了兩年時間放下舞蹈,轉而手執相機,Terry在2019年重新創作時,才發現攝影原來已然影響了他觀看世界的方式:
「平面的圖片,放在立體三維空間之中原來有所不同。例如我們的雙眼無法調色,但圖片可以,假如將這種元素放回現場表演又可行嗎?何謂調色?投身攝影後,在舞台設置、燈光、服裝的設計上,都令我對於顏色有了更複雜的思考。」這次名為《景 · 色》的創作,便尤其着重色調的呈現,首集《彡—毛鬙鬙》中以Terry 2019年的舞台作品為基礎再作發揮,導演Rose選擇以兩種對比色來凸顯視覺衝擊——舞者以鮮綠毛茸的形象出現,與封閉的紅色空間構成強烈對比,在連串的掙扎、依附與迎合之後,舞者從綠色的皮毛中蛻化,與外在的血紅混為一體。毛髮代表的熱情與不安,在色彩中融合為一。

從舊作的基礎再作演變,顏色在鏡頭的聚焦下化為主角,同樣曾在舞台上出演過的第二集《仨・角厝》,亦因為錄像而引申出別的呈現可能,例如由原作的鏡子改為用「鬼口水」象徵三口之家的關係。Terry笑言,這在劇場中完全沒可能做到,因為鬼口水的化學作用會吸收人體的熱力,以至拍攝過程中,舞者們每隔半小時就要沖熱水澡保溫,才能繼續拍攝。

「劇場上無法呈現的元素,我們可以在錄像上呈現,錄像的世界某程度上很假,因為我們可以『造』出來,例如在狼藉的佈置中只捕捉優美的一部分,相比之下劇場的世界則很真實,觀眾看到的場景全是實時發生的。但是錄像的世界可以帶領觀眾走到特定的空間,在走位上,劇場觀眾永遠鏡框式地凝定在一個角度,然而這次的錄像作品除了可把觀眾帶到表演者的身旁,也可以引領他們從一個表演者的視角出發,觀看整個空間,這也是現場表演與錄影作品不同的事情。」
身體美學影響鏡頭 劇場創作人的自省
影像擴闊舞蹈的呈現可能,身體的美學亦反過來影響鏡頭的表達。多年編舞的經驗,令Terry的鏡頭多了一份作為舞者的自覺,對肌理細節的刻劃因而更為明顯,甚至在身體以外的地方也顯露出作為舞蹈的動態。「舞蹈不只能利用身體來呈現,它也可能以物料、顏色等形式來呈現。」這次與創作團隊首次合作,攝影、道具、剪接、燈光等,全由來自不同範疇的創作者參與,為短片帶入舞蹈以外的視角。在籌備影片時,他們就概念構思到呈現方式共同商討,令劇場中難以實現的畫面,能夠以有限的資源與視角出現在鏡頭之中。

由個人對毛髮的恐懼推及家庭,創作團隊特別用黏液代表至親之間的關係,映射身體與身體的拉扯,探討我們如何用身體演繹恐懼;第三集《卅》則訴說香港的藝術生態,掛在劇院上空的人偶,失去靈魂,卻又在擺動的時候自成一種舞蹈。Terry指,原本影片中打算以假人玩偶作為懸吊的道具,然而出於成本的問題,團隊最終用膠紙包出人型,切合原先所想的視覺效果。他因此讚揚影片的製片及導演Kitty善於組織和協調,能夠將編舞的世界以更好的方式呈現給觀眾。
創作這段錄像時,正值劇場因疫情而全面停擺。影片中獨舞的Terry,形容自身代表了一種在觀眾席上游移的危機,同時象徵表演者對於觀眾和劇場的懼怕:「如何面對這群彷彿死去的靈魂?假如劇場表演恢復的時候,它們就會變成觀眾。他們活生生在此,卻好像失去了靈魂。這也是一種創作人對自身的反問:面對這個死寂的空間,我如何從事創作?如何令觀眾踏進劇場後重燃生氣?我的作品本身不能影響空間,但人與人感染所產生的頻率(vibration),能在空間裏營造一種新的元素。」
鏡頭在觀眾席與舞台的全景,進一步聚焦至舞者的身體,最後更以鏡像反映舞者與觀眾的關係,或許兩者相對,本身也是一種自觀。「對身體美學的認知,會影響我置放鏡頭時的角度,有人認為我熟悉身體移動的速度和線條,但其實這只是基礎,當中還包含我對舞蹈美學的追求。」從鏡頭移動的速度和角度中,可以看出一種對舞蹈本身動態的掌握,Terry對此亦表肯定。「平常跳舞時,我單用身體表達,觀眾未必看得清楚,但當我以影像來呈現時,能夠把我心中的美加以擴大,讓觀眾更了解我觀看世界的方式。」

鬧市中的重新凝視 以真誠宣示多元生活
到了最後一集《山》,創作的視角從人的關係再行突破,面孔有如死神的四肢生物由自然走進城市。舞者沒在片段中現身,卻將舞蹈帶到日常,攝影者變成街頭的路人,劇場則擴大至城市,大眾舉起手機加以凝視的過程,成為了一場藝術觀賞以至對美學的重新認知。「因為疫情,街上的人越來越少,山上的人卻越來越多,好像把整個空間帶進了自然。」Terry與導演Kitty由此開始思考人與自然的關係。「這樣的現象令我希望進行這次的創作,探討不同生物在不同空間裏如何適應、搬遷,究竟是我們去適應本已存在於那個空間裏的事物,還是我們其實正在造成破壞?」

出現在鬧市的怪異生物,難免刺激慣有的生活,在人聲、車聲與攝影的快門聲裏穿梭,創作團隊沒有為創作留下特定的答案,反而表示觀眾能夠自由地觀看和詮釋。「我們所做的事情就是給予線索、設多道門讓他們走進去,就算他們看不到也沒問題,影片有影像也有聲音,有時視覺無法傳達的訊息,可以用聲音來訴說。」
四集間由個人走向城市,反映了創作者對藝術的追求中也包含着一份社會關懷。觀察近年的香港,Terry從香港人身上看到一種尋找寄託的需要,「有些人享受看Youtube時輕鬆自在的時刻,但有時也會希望有增值自己的空間和時間,所以我覺得大眾是有所渴求的,大家有股意識,有種渴望堅守或支持本土文化的力量在當中。」
在如此現象之下,Terry認為藝術所包含的真、善、美,正正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同藝術形式所構成的感官衝擊,就是為了告訴觀眾:生活是多元的。從《景 · 色》四集節目所展示的舞蹈與鏡頭元素,成為了創作團隊的集體創作,從Terry對自身新舊創作的重新想像,以及由之坦露的內在恐懼中,亦不難看到個體身處群體之中的對抗與掙扎,在這之中,創作人自身所說的「真」,更是剖析內心與面對外在環境時無法缺少的一環。將私密情感變成舞蹈錄像外顯,看似屬於個人的情感,其實亦為大眾所共有,藉由鏡頭互相連繫和安慰,或許正如Terry所言:「人是需要群體的,彼此的接觸、擁抱是重要的,即是當你真誠地擁抱一個人,而不只是用言語講述,當中的意義是不同的。」

曾景輝《景 · 色》(網上節目)
節目介紹及播放:https://www.lcsd.gov.hk/CE/CulturalService/Programme/tc/dance/programs_1390.html
(創作團隊詳細資料見影片結尾)
撰文、攝影:鄭思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