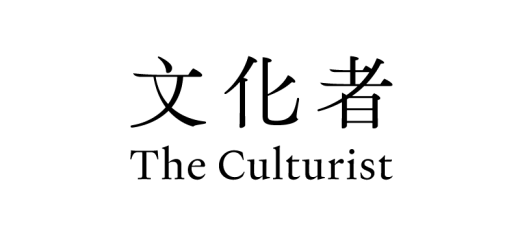可能因為在城市生活得太久有了慣性,每次坐船回到高松碼頭,都像是「回到人間」一樣鬆一口氣。而回到人間太久,就總想着跳上客船,隨便去瀨戶內海上的某個小島,也不用再去盯著地圖迷路,就那樣和島上的海灘、山洞、惡鬼、溫泉來一個不期而遇。
但這些島嶼看似與世無爭遠離「文明世界」,每個居民的生活卻都在被島外的世界影響着,島上作品的想像力也在被都市的重力牽引著——很多作品都在重現島嶼沒有的都市景觀,或是感懷島嶼與都市相異的生活方式。瀨戶內海同拯救了瀨戶內海的藝術祭都在世界的外面找到了與世界連結的方式。
李禹煥的巨人手杖

1992年,直島倍樂生藝術中心(Benesse Art Site Naoshima)在直島南部成立開設了藝術區,伴隨著瀨戶內藝術祭的開設,藝術區的網絡聲量越來越響亮。這裡除了安藤忠雄設計的、大名鼎鼎的網紅酒店,以及安藤忠雄設計的、大名鼎鼎的網紅地中博物館之外,另外有一間我很想去的,就是安藤忠雄設計的李禹煥美術館。
美術館座落在山中,背靠森林,面向大海,是一個十分安靜的去處。進門右轉就是一個狹窄的庭院,梳理整齊的日式石子地面上擺著一塊大石和一塊鐵板。讓我想起了京都龍安寺的苦禪庭院。但和龍安寺不同的是,這裡觀眾可以走進庭院,參與到石頭與鐵板的空間中——儘管工作人員反覆告訴你千萬不能踩上鐵板。
然而每一步走在石子地面上都會發出巨大的腳步聲。聲波在安藤忠雄設計的石壁內來回反彈,聽來極其吵鬧。我想這一定是有意為之,畢竟,極簡主義的一大特徵就是讓觀眾也參與到「創作」的概念中,從而孕育出無限的可能性。
庭院中央的鐵板一角微微翹起,讓我十分喜歡。鐵板正中央有一粒石頭碎片——以鐵板的角度來看,這塊碎片屑在中央渺小又堅強;以碎片的角度來看,這塊鐵板顯得廣袤無邊。配上了作品的名字《照応の広場》(照應的廣場),更感覺到「石頭與鐵板」相對於庭院,「石頭」相對於「鐵板」,「鐵板」又再次與「碎石」相互對應。
其實我一直以來都沒有太明白李禹煥的作品,雖然在香港看過很多次,但每次都是在白茫茫一片的畫廊空間裡,再搭配上其他極簡主義的作品——缺少語境的話,那各種各樣的色塊和石頭反倒更讓我摸不著頭腦。聽說安藤忠雄和李禹煥當初一拍即合,我也頭一次感到好像看明白了李禹煥的犀利之處。我以後再也不嘲笑某拍賣行總是賣不出去李禹煥的作品了。
逛完一圈到了紀念品商店,裡頭在賣印着《照応の広場》的明信片。明信片上的鐵板幹乾淨淨,上面一塊石頭都沒有——看來那塊碎石是某個遊客故意扔進去的。
第二天中午我和夫人離開直島,搭船前往高松港。
夫人突然「啊」了一聲,指著艙門上的圓形玻璃脫口而出:
「那個好像李禹煥的那幅畫!」
天氣晴好,為數不多的雲彩也像是棉花紮出來的肥兔子,緊緻地縮成一團。圓形玻璃上剛剛好反射到了那隻白色肥兔子的一角,搭配著蔚藍色的天空,煞是賞心悅目。
我問她像哪部作品,她也講不清楚。我想可能是《對話》,但也不確定。

(Dialogue, signed ‘Lee Ufan ’11′ (lower right), watercolour on paper, 38 x 59 cm, painted in 2011. Image courtesy of Christie’s)
我突然覺得,我其實依舊沒理解李禹煥,也許她才是理解了。
香港加油

男木島的一間參展民居的二樓是海景咖啡館,和式房間正中央的桌上擺著幾本厚厚的留言簿,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都可以留言(不過還是以中文為主)。我剛走進房間,就看到一名中國男生正襟危坐在桌前,出神地望著自己剛剛在留言簿上寫的話。
這時他女朋友走過來,見他表情凝重,便把手搭在他肩上,輕聲問道,「怎麼啦?」男生指了指留言簿:「我在糾正他們的話。」
等到兩人離開,我翻到留言簿的那一頁。最上面寫著「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和「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下方有另一種顏色的筆以英文寫著:
「Hong Kong is part of China, not matter how hard you try!!!」
我很想追上去同他說,「not matter」是文法錯誤,應該是「no matter」。但我又憶起剛剛他臉上那壯士斷腕、大義凜然的表情——他應該非常堅信自己所說的話吧。想到他如此真誠地相信自己,我一時不忍心再去揶揄他。
還有一次,是一間在小豆島的民居作品前,負責給訪客印章的是一位日本老爺爺。他見我用生硬的日語同他打招呼,就問我是哪裡來的。我說是香港,他嘆了口氣道:
「香港いま大変だなぁ!」(香港現在很糟糕啊!)
我說,是啊。
老爺爺沈默了一下,之後用生硬的英語說:
「I wish you free and peace.」
我不知道如何答他,只有不斷鞠躬行禮,向他道謝。
撰文、攝影:楊小虎